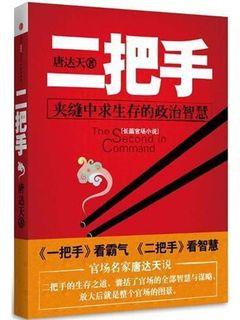杏書首頁 我的書架 A-AA+ 去發書評 收藏 書簽 手機
简
第六章 壹紙調令帶來的變局
2024-10-28 19:32
權力的爭奪,往小裏說是個人與個人之間的爭奪,往大裏說是各個利益派別之間的爭奪。這個派別的帶頭人上去了,從上到下,大家都跟著沾光;如果這個派別的帶頭人被壓下去了,或者是出了什麽問題,大家都跟著遭殃。現在,吳國順最想做的就是兩件事,壹是積極支持何東陽當上市長,二是把姚潔推翻。
1.家庭是最不講理的地方
幾天過後,那條老農被打的新聞已經在網上火爆起來了,許多地方報紙也做了轉載,整個事件查清了,打人者是南城區城管分隊副隊長胡亞生。何東陽聽到這個名字驚呆了,胡亞生?他的小舅子也叫胡亞生,這個打人的胡亞生會不會是他呢?
說到小舅子,他的確沒有多少好感,在上中學時就不好好學習,成天跟幾個小混混在壹起,不是喝酒滋事,就是上網玩遊戲。上大學無望,丈母娘求上門來,讓他給安排去當兵,將來退伍後好安排工作。他知道,現在城市當兵競爭很激烈,沒有特殊關系,想當兵也當不上。當兵已經失去原來的意義,由義務奉獻成了變相的曲線就業。他經不起丈母娘的嘮叨,更經不起胡亞娟天天吹枕頭風,最終還是安排小舅子當了兵。大前年退伍後,他的事情又來了。妻子胡亞娟受丈母娘的攛掇,讓他想個辦法把胡亞生安排到公安局去上班。
他有些不高興地說:“這是不是胡亞生的意思?”
胡亞娟說:“妳也知道,他沒有學下什麽東西,到別的地方去也不太合適,到公安局去抓個壞人、破個案子倒還行,他也喜歡幹那壹行。”
“妳告訴他,公安局屬於省公安廳直屬管理,他們要是沒有招人名額,我也辦不到。另外,市裏會對他們這些人做統壹安排,他發什麽愁?”
“這也不是愁不愁的事,誰不想著有個好壹些的工作?妳看著辦吧,反正是妳的小舅子,想幫就幫,不想幫也沒辦法。”
他不喜歡妻子用這樣的口氣跟他說話,更不喜歡丈母娘總是想利用他的關系走後門,卻不要求她的兒子去努力。沒過幾天,丈母娘叫他去吃飯。在飯桌上,胡亞生說:“姐夫,公安局進不去的話,暫時不進也行,聽我壹個戰友說,城管大隊現在缺人,妳就讓我去城管大隊吧。”
何東陽說:“妳們這壹批退伍軍人市裏已經做了統壹安排,壹部分人被安排到市化工廠去上班,壹部分人安排到市園林綠化隊。就這兩個單位妳選吧,選中哪個我可以幫妳說說。”沒想他的話還沒說完,丈母娘就不高興了。
丈母娘說:“要是在這兩個單位做選擇,他還求妳這個姐夫做啥?”老丈人重重地咳了壹聲,示意丈母娘不要再說下去了。何東陽假裝沒聽見,也不吱聲。這頓飯吃得很不開心,沒想到回了家,胡亞娟又跟他鬧起了別扭,說他當了副市長後,眼裏沒有她的家人。
何東陽生氣地說:“什麽話?沒有妳的家人我還上妳家做什麽?妳弟想當兵我就安排當兵,現在回來了,能統壹安排就業就不錯了,還挑三揀四的,妳們以為副市長的權力有多大?現在每個單位的編制都很緊,妳強行安排壹個人,跟著就會傳來壹大堆閑言碎語,妳們只顧自家的事,怎麽就不想想我的感受?”
“妳辦成辦不成也有句好話,哪有妳這樣的,壹句話就把人拒之於千裏之外了。難怪媽媽說妳,當了大官就瞧不起我們壹家人了。”
“這是什麽話?樣樣依了妳們就是瞧得起妳們?達不成妳們的心願就是瞧不起妳們?”
“妳看妳,還沒有說三句話,就妳們妳們的,這不是明顯地把我們壹家人與妳劃分開了嗎?還說不是哩。”他不想與妻子吵,只好說問問再看,還不知他們有沒有編制。
何東陽雖然心裏極不痛快,但又不想回家聽胡亞娟的嘮叨,只好勉為其難地將小舅了安排到了城管大隊,這才算平息了家庭內部的矛盾。當時他還考慮丈母娘家住東城,就把小舅子安排離家近壹些的地方,好對家裏有個照顧。
這個打人的胡亞生在南城,而且是分隊的副隊長,他的小舅子在東城,而且是壹個普通的工作人員,不可能是同壹個人吧。但是,現在既然事情發生了,他也管不了那麽多,只能對事,不能對人,如果真的是他的小舅子,也好讓他長長記性,先學學怎麽做人。
晚上回了家,胡亞娟正在收拾打扮,見他來了,就高興地說:“老公,我今天不做飯了,我媽鹵了妳最愛吃的豬蹄子,下午就給我打了電話,說讓我們壹起去吃。”
他心裏咯噔了壹下,馬上明白了,那個打人的胡亞生肯定是自己的小舅子,否則,丈母娘鹵豬蹄子也不會這麽湊巧。他知道丈母娘的飯好吃難消化,明明是鴻門宴,還必須要去,如果不去,必定會引發新的家庭矛盾。
來到丈母娘家,他壹進門就聞到了壹股濃濃的肉香味,那是丈母娘的拿手好戲,只有她才能調出那樣的味道,才能鹵出對他胃口的豬蹄子。與丈母娘和老丈人打過招呼後,胡亞生從裏屋出來了,也向他打了壹聲招呼。胡亞生長得高高大大的,看上去壹表人才,但是言談舉止中卻免不了有些小痞子的味道。
何東陽問:“最近工作還好嗎?”
胡亞生不好意思地笑笑,說:“還行。”
胡亞娟說:“還行什麽?現在成了名人了,都上網絡了,登報紙了。”
胡亞生的臉就刷的壹下紅了。
丈母娘說:“亂說什麽?吃飯吃飯。”
何東陽壹聽就明白了,他們不道破,他也不願意多問。
等壹大盆香噴噴的鹵豬蹄上了桌,胡亞生拿過塑料手套,給桌上每人發了壹雙。丈母娘說:“吃吧,趁熱吃,我鹵了壹大鍋,吃完了再上。”
何東陽看老太太挺辛苦的,等丈母娘落座後,不失時機地誇獎說:“我吃過的大餐也不少了,從沒有哪壹家的豬蹄子有媽做的這麽好吃。”
丈母娘經市長女婿壹誇,也高興地說:“那妳以後想吃了,就讓亞娟說壹聲,媽給妳們做。”
胡亞娟說:“媽,妳要拿壹手,不能他想吃了就做,等到他饞極了,才做壹頓,這樣他才吃不膩,每次都覺得好吃。”
丈母娘笑著白了壹眼胡亞娟,說:“妳還以為是從前,幾個月都吃不到肉,現在生活這麽好,普通人都不會饞極,他堂堂壹個市長能饞極?”
何東陽說:“那也說不準,多多每次來了,吃什麽都覺得不過癮,就想吃姥姥做的鹵豬蹄。”多多是何東陽的兒子,現在在省城讀大學,小的時候基本上都由姥姥帶著,從小就吃慣了姥姥做的飯菜,現在每次假期回來,就想吃姥姥做的飯。壹說到多多,老太太的話又多了,問他來電話了沒?身體怎麽樣?胡亞娟就接過話回答說,老太太為帶多多費了不少心血,對外孫的感情反而比我這個當媽的還深。何東陽聽得出來,胡亞娟明裏是貶自己,實際上是為了擡高她媽的功勞。不過話說回來,她說的也是實話,何東陽每每想起這些,覺得虧欠丈母娘的太多了,所以,有時丈母娘在他面前嘮叨上幾句,他也不太計較。
吃過飯,何東陽覺得該談正事了,就看著胡亞生,想問壹問他的副隊長是怎麽得來的,便說:“妳進步還挺快的,已經成了分隊副隊長了?”
胡亞生的臉壹紅,不好意思地說:“還不是在姐夫的關懷下才進步的嘛。”
何東陽立刻明白了,肯定是胡亞生打著自己的幌子走了關系,他們單位領導為了拍自己的馬屁才提拔了他,否則,憑他的表現根本不可能。他不想道破,又問:“剛才妳姐說妳上網絡上報紙是咋回事?”
胡亞生這才說:“姐夫,妳可要幫幫我。前兩天網絡曝出那個打了七旬老人的城管就是我……”
老丈人瞪了他壹眼,打斷他的話:“妳還好意思說,我的老臉都讓妳給丟盡了。”老丈人是個老實人,不愛說話。此刻,他能打斷話來指責兒子,說明他真是生氣了。
何東陽馬上打圓場說:“爸,妳別生氣,先讓亞生把話講完。”
胡亞生這才又說:“那天的事情是這樣的,那個老漢前壹次吆喝著毛驢車從主街道上過來的,我警告過他,這次他又走了這條路,我讓他拉回家去,並嚇唬他說,他要不返回去我就摔他的菜。我本來是想讓他承認錯誤,沒想這老漢太犟,說,妳敢?我就真摔了下去。他不幹了,上來扯住我的衣服,我才動手打了他兩個耳光。沒想到這件事鬧大了,不知被什麽人捅到了網上,雖然沒有提名道姓,但上面來人壹追查,還是查到了我。聽領導的意思,還要撤我的職,司法部門還要介入,這樣壹來,這飯碗能不能保住都很難說。”
何東陽說:“妳呀!妳是壹名執法人員,怎麽能動手打人?而且打的又是七十多歲的老人。現在惹出了禍,才知道後悔了?”
丈母娘說:“可不是嘛,他早就後悔了,這幾天飯都吃不下去了。如果飯碗真丟了,以後可咋辦?東陽,妳是當哥的,妳弟做得不對,妳批評教育,但無論如何別讓公安局抓進去。這壹抓進去,再放出來,人就不是原來的那個人了,工作沒了,對象也沒了,恐怕壹輩子都會在人前擡不起頭來。”
老太太繞了壹個大圈,就是想讓他為胡亞生幫幫忙,何東陽不好直接拒絕,就故意說:“妳們可能還不知道吧?那天,那個挨了打的老人家來市政府堵住了我的車,我親口答應了他,要查清楚這件事,對打人者要給予嚴懲。妳看妳,胡亞生,惹了這樣大的禍,也不早告訴我壹聲。”
老太太接了說:“他還不是怕給妳添麻煩嘛。現在紙包不住火了,只好求妳出面說說,讓他們單位內部批評教育壹下就行了,別再讓公安局插手了,怎麽說他也是多多的舅舅,妳就看在多多的面子上幫幫他吧。”老太太說著,就吸溜吸溜地哭了起來。
何東陽聽到她壹哭,心也軟了許多,雖然他對胡亞生的這種做法非常生氣,但他畢竟是孩子的舅舅,有了這層關系在裏面,許多東西想繞開也很困難。他只好勸慰老太太:“媽,妳別哭了。既然事情發生了,我們就盡量挽回。至於亞生的工作問題,我可以向妳保證,不會受到影響,別的方面,可能會受點兒影響,不過,吸取壹些經驗教訓也沒有什麽不好,讓他長點兒記性。”
胡亞娟也趁機說:“媽,妳放心吧。亞生只不過犯了這麽個小錯誤,還不至於被開除公職。再說了,東陽現在還在副市長這個位子上,只要他們知道亞生是東陽的小舅子,下面辦事的人就不會太過分。”
何東陽壹聽這話很不高興,胡亞娟怎麽這麽說話,這不是明顯地在鼓勵胡亞生為虎作倀嗎?他看了她壹眼,本想說幾句,又覺得這種場合說了不好,就沒有吱聲。
回到家裏,何東陽覺得有必要向胡亞娟提個醒,就問她:“胡亞生的副隊長是怎麽壹回事?”
“什麽怎麽壹回事?他表現不錯,單位領導覺得應該重用他,就提拔了他。”
何東陽正色說:“亞娟,妳給我說實話,妳是不是暗中走了關系?”
“什麽暗中走關系?說得難聽死了。我只不過在壹次偶然的機會見到了他們城管隊的隊長,向他問了壹下胡亞生的情況,希望他多多關照壹下,並沒有說讓他提拔。”
“亞娟,我給妳明確地說壹聲,以後不許妳再這樣。妳是領導幹部的家屬,妳這樣過問妳弟弟的領導,並叮囑他要關照妳弟弟,他會怎麽想?他肯定會認為妳想讓他提拔妳的弟弟,他不提,怕是我授意的;提吧,又勉為其難。傳出去,讓別人怎麽想?”
胡亞娟的臉上掛不住了,就說:“妳看妳,我既沒有提妳的名字,更沒有打妳的旗號,我只問問我弟的情況就不行了?難道我嫁了壹個副市長,我連關心弟弟的權利也沒有了嗎?”
何東陽盡量心平氣和地說:“不是說妳嫁了我就不讓妳關心弟弟,妳的弟弟也是我的弟弟,我不是不妳讓關心,但不是像妳這樣的關心,妳這不是真正的關心,而是害妳弟弟。”
胡亞娟“哦唷”了壹聲:“領導的話就是有水平,可我就是壹點兒也聽不懂,好像妳的關心才是真正的關心,別人的關心都是害人家?我問妳,妳關心他什麽啦?比起我媽媽關心妳兒子來,妳對亞生的關心能有多少?”
女人死攪蠻纏的時候,妳絕對不能順著她的話去說,否則,妳就會進到她那混亂的邏輯圈套中走不出來。他不接她的話茬,只講著道理說:“比如說,妳今天當著他的面說的那些話,就不應該,那樣愛他,會助長他的優越感,反而會害他。”
“哪些話?我說哪些話助長了他的優越感,會害了他?難道我們都是害他的,只有妳壹個人是關心他的嗎?”→文¤人·$·書·¤·屋←
“妳當著他的面說,只要他們知道亞生是東陽的小舅子,下面辦事的人也不會太過分。這種暗示性的話,對他沒什麽好處。”
“難道我說的不是真的?難道妳要否認他是妳的小舅子嗎?行!何東陽,何市長,妳要真的覺得有這樣壹個小舅子丟了妳的臉,影響妳升官,妳可以不認他,可以斷絕與他來往,但是妳沒有權力幹涉我認我的家人。”說著說著,竟然嗚嗚咽咽地哭了起來。
何東陽壹看胡亞娟這麽不講道理,無心再說了,只好連連說:“好了好了,越說越離譜了,什麽斷絕來往,什麽不認他,說這些傷感情的話做什麽?妳看電視吧,我到書房裏看壹會兒文件。”
何東陽雖然嘴上說得很平靜,心裏卻十分惱火,他沒有想到胡亞娟越來越俗不可耐,越來越不可理喻了。勞累了壹天,本來想在家庭這個溫暖的港灣裏小憩,之後再投入到明天的工作中,可誰知家庭有時候卻是壹個最不講道理的場所。晚年的托爾斯泰就是因為家庭不和諧,才發出了“人生最大的孤獨就是臥室裏的孤獨”的感嘆。
來到書房,他並不是想看什麽文件,而是想在這裏平靜壹會兒。他點了支煙,吸著,想著,覺得心裏有壹種說不出的委屈。要是壹個普通的工人、普通的公務員,遇上這麽不講理的老婆,可以同她吵,同她鬧,可他不能,他必須讓著她。正因為這壹而再、再而三的忍讓,讓她得寸進尺,越來越不可理喻。好在他的官不大,權力也有限,倘若他的官位再高壹些,權力再大壹些,說不定她還會幹出什麽事來。
第二天壹上班,秘書長潘多文敲開了他的辦公室,何東陽向他點了點頭,示意他坐下來說。
潘多文就坐在了辦公桌對面的椅子上,說:“我已經安排明天早上去鄉下慰問那位上訪的老人,讓城管大隊也去,順便讓他們買壹些滋補品帶上。我想請示壹下何市長,需不需要通知媒體參與?”
何東陽覺得潘多文不愧是秘書長,問題就是想得周到,便問他:“妳覺得有沒有必要通知他們去?”
潘多文說:“如果明天讓胡亞生壹同去的話,就不要通知媒體了,最好不要讓媒體知道具體的人。如果胡亞生不去,就讓媒體去報道壹下,也算是對社會輿論作壹個交代。”
何東陽知道潘多文完全是為了考慮胡亞生的聲譽才這麽安排的,便說:“解鈴還需系鈴人,讓他親自去賠禮道歉,老人家心裏會平衡些。再說了,這對胡亞生也是壹次吸取教訓的極好機會,不能讓他錯誤地認為,他是我的小舅子就可以為所欲為。”
“何市長也不必擔心,我已咨詢了有關司法部門,這只是工作方法上的不當,還構不成司法處理。另外,城管大隊領導也表態了,由他們批評教育就行了,司法部門沒有插手的必要。”
何東陽心裏當然清楚,潘多文在有意替他擔當,如果他們不知道胡亞生是他的小舅子,處理的結果遠遠不是這樣的。雖然他沒有有意授權於誰,而下面辦事的人都礙於他的面子,想把大事化小,小事化了。但任何事情都得有個限度,不能太過分了,太過分了,必然會引起民憤,必然會適得其反。想到這裏,便說:“光單位批評教育還不夠,必須要做出行政處分,這樣才好給社會壹個交代,對他本人也是壹次教育。他現在不是分隊的副隊長嗎?像他這樣,還怎麽繼續當?”
“我明白了,何市長,那我走了?”
“那妳去吧,該怎麽辦就怎麽辦,不要顧及我。”
潘多文走後,何東陽覺得輕松了許多。這件事如此處理,也算比較圓滿,既對社會輿論有了壹個交代,妻子壹家人也能接受。
剛點了支煙,還沒有吸上兩口,信訪辦的高永信匆匆進來了,他壹看高永信臉色不大對勁,就知道麻煩事又來了,忙問:“什麽事?”
高永信垂了頭說:“我幹了壹件壞良心的事。”
“什麽壞良心的事?”
“李瘋子患了癌癥,已經晚期了。那天我們幾個人把他送到精神病醫院後,醫生悄悄告訴我,他已經患癌癥了。放他出來,就是想讓他與家人、親友們最後聚聚,怎麽又把他送回來了?我壹聽傻眼了,只告訴醫生,要不是首長來視察,遇到這麽大的政治活動,我們也不會把他送回來的。回來的路上,我的心裏壹直很糾結,我都是快退休的人了,幹的什麽呀?我們的政府,為什麽這麽害怕聽到反面意見?為什麽這麽害怕上訪者?快回到金州時,我實在拗不過自己,就讓其他人回來了,我壹個人又去了趟醫院,親自把李瘋子給接回來了。回來後,我就與他的家人壹起把他送到了市醫院,檢查的結果是,癌細胞已經擴散了,估計他在人世的日子也不會太多了。”
何東陽心裏壹陣陣絞痛。“我們的政府,為什麽這麽害怕聽到反面意見?為什麽這麽害怕上訪者?”高永信的詰問像刀子壹樣剜著他的心,也常常困擾著他,他卻無言以對。在他所受的理論教育中,從來都是人民的利益高於壹切,要與人民群眾心連心,要接受群眾的監督。但理論與現實結合的時候,又成了另外壹回事。因為壹些反面意見,會影響到決策者的政治前途,如果接受了他們的意見,容忍了他們,就意味著要放棄自己的壹切,包括權力、地位,這就人為地加劇了領導者與被領導者之間的對立與矛盾。而他和高永信,在融入到這個利益集團之後,就會不自覺地維護這個團體的利益。維護團體的利益,其實也就是在維護自己的利益。正因為如此,他和高永信壹樣,無形中成了扼殺李瘋子的幫兇。說到底,他和高永信只不過是這個利益鏈條中的壹個節,誰都很難掙脫,除非妳要放棄所有的壹切。
高永信緩緩地從口袋中拿出壹張折疊整齊的紙,打開,放到了他的面前:“我最近身體不太好,老了,畢竟五十多歲的人了,想申請內退,希望組織能批準。”
何東陽的腦子“嗡”地壹下,他知道,這件事可能對高永信的觸動太大了,才下了決心要放棄所有的壹切,求得壹種心靈上的平衡。而事實上,這件事不僅對高永信,對他的內心也是壹次極大的沖擊。現在,李瘋子的生命已經無可挽回了,如果……高永信就這樣走了,他的心裏實在有些承受不起。畢竟,高永信是他的部下,他不能讓他帶著這樣壹顆破碎的心離開工作崗位,就此退休。他將退休報告輕輕推到高永信面前,說:“老高,其實我的心與妳壹樣。有些事,妳不願意,我也不願意,但這又不會因我們的主觀意誌而轉移,沒有辦法,誰讓我們在同壹個體制內?”
高永信又將內退報告推了過來,說:“正因為如此,我才想解脫,我再也不願意經受這種內心的折磨了,再也經受不起了。”
“老高,內退了,就能解脫妳內心的折磨嗎?不能的。有些,過後了才知錯,妳是,我也是。妳可以請假休息調整壹下,或者找個出差的理由,出去散散心。內退真的不行,放了妳,我的心裏更難受。”說著又將報告推到高永信的面前,“收起來吧,我再也不給妳添壓了。老高,人心都是肉長的,我給妳添壓的同時,我何嘗不是與妳壹樣的心情?”
2.月色中的野合
又是壹個雙休日,吳國順的老婆去參加老同學聚會,兒子到學校補課,他正好有了時間,就想與田小麥纏綿壹下。盡管他懷疑田小麥傍上了蘇正萬,想起來像吃了只蒼蠅壹樣惡心,但壹想到她的身體,想到她在床上的千呼萬喚,他就不由得壹陣興奮,全身充滿了活力。他恨她,又無法徹底放棄她。有時,就是帶著這種恨,在汗水與肉搏中又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愛。他由此而感慨,人真是個難以理解的怪物,心裏壹方面在恨她,另壹方面又想進入她。壹旦進入後,又覺得她是那麽的美好,是那麽的無可替代。
記得上次與她相約,是在壹個月前。他與幾個朋友喝酒時,收到了她的信息:“妳在幹嗎?”壹看到她的名字,心裏就壹陣莫名的激動,馬上回了信息:“與朋友喝酒。妳呢?在忙什麽?”信息馬上又來了:“我在金海馬唱歌,無聊死了。妳散夥了給我電話。”他壹看到這樣的信息,就知道她想見自己,只好對朋友說,有事要回家。壹個開車的朋友想放開膽量好好喝壹場,就把車鑰匙給他,妳開車去,明天早上,我到文廣局去取車。
吳國順完全有能力自己買壹輛車的,但他不想買。他現在還是體制中人,又是官員,太張揚會引起別人的猜忌。更重要的是,他還享有坐公車的權力,雖然這種權力暫時被人篡奪了,但隨著時間的推移,壹定會奪回屬於他的那份權威和尊嚴。
吳國順上車後,給田小麥發了壹條信息:“十五分鐘後,妳下樓,我來接妳。”發完信息,就開車上了路。金州的夜晚褪了白天的浮華,卻要比白天看起來陰柔了許多,閃爍的霓虹燈光中多了幾分曖昧色彩,讓人平添了壹種欲望的沖動。車繞過天橋,向南壹拐,就在很遠的地方看到了“金海馬”三個立體感很強的大字,在燈光變幻中放出不同的色彩。這個地方他過去經常來,都是老板們請他來唱歌。他特別不喜歡這種氛圍,為了不駁對方的面子,又不得不到這裏待壹會兒。現在,大權旁落後,昔日那些酒肉朋友壹個個遠離了他,飯局少多了,正好落個自在。車到金海馬門口的廣場,他壹眼就看到了等候他的田小麥。田小麥今天穿得特別隨意,上身著壹件白色長袖衫,下身穿著緊身黑色褲,腳蹬壹雙紫色長靴,外加壹個黃色披肩,壹個大包,高綰起發髻,整個人就顯得身材火辣而又高挑。
他將車開到她面前,打開窗戶說:“請吧,小姐。”
田小麥“哇噻”了壹聲,上了車才說:“沒想到我們家的小順子也玩起了酷,這是誰的車?”
吳國順忍不住咧起大嘴哈哈大笑了起來。
田小麥說:“傻笑個什麽?”
吳國順邊笑邊說:“妳怎麽叫我小順子?”
田小麥嘻嘻笑著說:“叫著覺得親切,好玩唄。”
“小順子是我的小名,這世上除了我們村裏的長輩這麽叫過我,還沒有人再敢這麽叫,真是個小妖精,沒大沒小的,以後不許叫。”
“原來是妳小名?真好玩!為啥不能叫?”
“讓人聽到了多不好?”
“原來妳也有怕?妳不讓我叫,我偏要叫,小順子,小順子……”
他被田小麥逗樂了,就嘿嘿笑著說:“小妖精,再叫看我怎麽收拾妳!”
田小麥就將頭湊過來悄悄說:“好呀,本姑娘等著妳收拾。”
“現在開車,等回到家裏再說。”
“妳還沒有回答我的話,這車是誰的?”
“是我壹個朋友的,他喝酒,怕出事,我只好把車開來了。”
“要不,開車兜兜風再回去,剛才在KTV烏煙瘴氣的,悶死了,是壹個老板請廣告部的客,他們硬拉上了我。”
吳國順壹聽心裏酸酸的。過去他在廣電局主事時,管理上很嚴格,絕不允許廣告人員吃廣告客戶的飯,決不允許記者搞有償新聞。沒想到,不到幾個月的工夫,物是人非,好不容易形成的良好風氣就這麽敗壞下去了。也罷,壹朝天子壹朝臣,等到自己坐鎮了,再來次廢舊革新。
田小麥見他沒有吱聲,便問:“妳在想什麽?”
他這才問:“到什麽地方去兜風?”
“我們去看看莊稼地好不好?”
“好的。”說著就將車開到了西環城公路上。這條公路上車輛不多,路的兩邊,壹邊是城市,壹邊是田野。白天,農村的人到城裏來逛街,晚上,城裏人又到田野來散步。時令到了秋天,天氣有點兒涼,田野裏的風景少了,來田野散步的人寥寥無幾。他把車開到田野的土路上,壹直開到了壹片小樹林裏,才與田小麥下了車。
秋天的月亮照著大地,微風壹起,旁邊的那片玉米就跟著搖曳了起來,發出沙沙的聲音。田小麥來到田埂上,高興地說:“真美喲,好壹片田園風光。”
吳國順隨口吟誦道:“郭外秋聲急,城邊月色殘。”
她接了道:“瑤琴多遠思,更為客中彈。”
“妳也會?”
“王昌齡的詩,過去讀過。”
他看了她壹眼,月色朦朧中,田小麥身材顯得越發火辣,胸脯挺得很高,腰呈壹抹弧,臀便自然地翹了。他不由自主地走過去,從後面攬腰抱住了她:“冷嗎?給妳暖和壹下。”
田小麥咯咯地笑著說:“不冷。”
“不冷也要抱!”
她故意將屁股撅了幾下,說:“我就知道妳想抱,抱抱抱,我讓妳抱!”
吳國順被她刺激得渾身膨脹了起來,想起小時候在鄉村看公馬和母馬交配時,小母馬總是要尥幾個下蹶子,公馬總是樂此不疲,壹直將母馬調戲得渾身發軟了,才能服服帖帖地讓公馬的擺布。其實,人與動物也有相同的壹面,也有主動與被動之分,經她這壹尥蹶子,反而刺激了他,他緊緊地攬著她的胸,親吻著她的頸項和耳朵。很快,聽到她的呼吸聲加重了,並且還發了壹聲細細的呻吟。而這呻吟聲,又讓他更加亢奮,扳過她的身子,壹下緊緊地親住了她那散發著香味的小嘴兒,兩個人的身體就從正面緊緊地貼到了壹起。他的手就從她衣服中摸了下去,光滑的背,細柔的腰,飽滿的臀,手到處,處處是風景。她的身子就這樣被他越摸越軟,還不時顫動著。他騰出手解她的褲扣,剛將褲子扒了壹截,她突然伸過手拉住說:“到家好嗎?”
“野外好,我們還沒有在野外好過,就在野外。”
“不會有人吧?”
他環顧了壹下四周,很安靜。他拿掉她的手,又將褲子朝下拉了壹截,他感到了從她身上散發出來的熱量,還有壹縷淡淡的體香。風從兩人的身上輕輕掠過,吹到玉米葉上沙沙作響,月光如水般灑在他們的身上,又被他們搖成了碎片。她輕笑著說,在這野外我還是第壹次,真刺激。他說,妳掉過身去更刺激。於是,她又掉過了身,他從後面抱緊了她。很快地,那呻吟聲就融入到了曠野的沙沙秋風中。
此後多日,吳國順壹想起那天晚上的野合,就會產生壹種莫名的興奮。場景的轉換,能讓人產生新鮮感。他想,有了這壹次,以後還可以繼續。他已經對田小麥的身體有了壹種依賴,這種依賴,就像酒鬼於酒、煙鬼於煙、賭徒於麻將壹樣。盡管他無法接受她與蘇正萬的曖昧,有時候想起來有壹種說不出的恨與痛,但壹想到她的身體,他還是止不住渴望與興奮。
這天早上,等妻子出了門,他就迫不及待地給田小麥打了壹個電話,沒想到她卻關了機。過壹會兒又打,還是關機。心裏便想,這小婊子是不是與蘇正萬在壹起鬼混?≮更多好書請訪問Zei8.me 賊吧電子書≯
吳國順壹想到蘇正萬,心裏就像吞了壹只蒼蠅。真是個垃圾,電視臺的美女如雲,他為什麽不勾引別的,偏偏來撬他的?不知是他有意挑釁,還是真的喜歡田小麥?無論是挑釁,還是真的喜歡,他都覺得蘇正萬不應該拆自己的臺,更不應該利用職務之便迫使女下屬就範。君子報仇,十年不晚。他想等自己的計劃成功了,放翻了姚潔,再來慢慢收拾蘇正萬,要讓他為此付出沈重的代價。
他的計劃正在實施過程中,三天前,馬民說他已經從邵大鵬那裏套來了話,邵大鵬給姚潔送過40萬元和壹塊金表。邵大鵬說,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,我給她的最終還是加在工程款裏。吳國順明白,權錢交易的背後就是政府來埋單。近年來,各地的豆腐渣工程層出不窮,這邊的橋梁剛剛倒塌,那邊的樓房又壓死了不少人,說到底,這都是腐敗引起的。他不能說自己有多麽幹凈,他也不是什麽好鳥,也曾利用手中的權力在工程建設中謀取過私利,但相比姚潔,他沒有這個女人那麽貪心,更沒有她那麽膽大包天。他問馬民錄音了沒有?馬民說音是錄了,就是怕這錄音流出去,邵大鵬決不會放過他。他覺得馬民說的也是,就點點頭讓馬民先把錄音帶保存好,千萬別丟失了,然後再想想有沒有別的辦法,既不能讓邵大鵬懷疑到馬民,還要把姚潔的事反映出來。
這可是壹顆定時炸彈,有了這顆炸彈,足以置姚潔於死地。他感到了必勝的把握,也看到了希望的曙光。
吳國順看了壹會兒電視,到了十點多,又給田小麥打了壹個電話,還是沒有開機。他內心裏產生了壹種按捺不住的沖動,他要直接到田小麥住的地方去找她,他要親自證實壹下自己的判斷,看看她究竟在幹什麽。是自己多疑,還是她有事?
出門叫了壹輛的士,不壹會兒就到了幸福花園小區。壹來到這個地方,他就心潮起伏,感慨萬千,在這個地方,他已經與田小麥好了兩年多了。在這兩年多的纏綿中,他在經濟上付出了很多,她家要買房子,他給了20萬,平時給她買這買那,也花了不少。有時候,經濟與感情是成正比的,經濟上付出得越多,情感上投入得也越大。情感不等於錢,但錢可以表達情感。錢是妳付出勞動得來的,是壹種價值的符號,妳完全可以用它謀取幸福。當妳把它付給某壹個人的時候,就意味著將妳的情感也投入到了其中,錢也就成了情感。壹個人,倘若他說在情感上付出了很多,但是從來舍不得在經濟上付出,妳會認為他說的是真的嗎?顯然不可信,因為他最愛的是錢,他把最愛的東西儲存起來,舍不得花在他所愛的人身上,這種愛充其量也只是口頭的愛,沒有變成真愛。倘若有壹天沒有了這愛,他只感到遺憾,決不會心痛,因為他沒有損失什麽。而對於吳國順來講,如果有壹天真的與田小麥分道揚鑣了,他不僅會感到遺憾,也會心痛,因為他付出過情感。
來到幸福花園裏面,看到人工湖中假山聳立,流水潺潺,花草卻有些敗謝,綠地有些微黃。北方的秋天,總給人壹種淡淡的淒涼。就在吳國順從人工湖中穿過時,他看到了壹輛黑色的小車從旁邊的小路上開走了,他壹眼就認出了車牌號,是蘇正萬的。霎那間,他血脈賁張,臉上壹陣發燒。婊子,真他媽的婊子!難怪她壹直關機,原來她是留蘇正萬在這裏過的夜。他在心裏恨恨地罵著,大步向她住的C號樓走去。記得他剛剛拿到這套房子的鑰匙時,第壹個想到的就是她,他寧可與老婆孩子住舊房,卻把豪華社區的房子讓給她,沒想到她卻把他的房子當成了與別的男人鬼混的場所,是可忍孰不可忍!他匆匆來到C號樓,正準備摁門鈴,聽到有人下樓來,他就等到那人出門的時候時直接進了門。到了八層,來到802號門前,他側耳聽了聽,裏面有電視的聲音,他這才摁了門鈴。
他的心咚咚咚地跳著,雖然他不知道接下來將會發生什麽事,但他知道在他與蘇正萬之間,沒有調和的余地,有他就沒有蘇正萬,有蘇正萬就沒有他。他必須讓她做出明確的表態,否則,就讓她滾蛋!
他聽到了開門的聲音,她的抱怨聲也從門裏傳出來:“妳怎麽又來了?是不是落下什麽東西了?”
“是的,我落下了東西。”
“怎麽是妳?”
“怎麽就不能是我?這是我的房子,我難道沒有來的權利嗎?”
她壹轉身,回到了房間。他進了屋,壹轉身,砰的壹聲關上了門,房間裏立刻充滿了火藥味。
田小麥穿著壹身睡衣坐在沙發上,茶幾上的煙灰缸裏殘留著幾只煙蒂。他渾身壹陣戰栗,過了半天才說:“他昨天在這裏過的夜?”
“沒有。”
“背上牛頭不認賬!我明明看到他開車出去了,還想抵賴?妳給我說,這煙頭是誰的?”
“我抵賴什麽?早上他打電話叫我去加班,我說我感冒了,他給我買了點兒感冒藥,送來坐了壹會兒。這有什麽奇怪的?”
“妳就編吧。妳早上壓根兒就沒有開過機,還打什麽電話,打妳個鬼!”
“妳這人怎麽這麽說話,他打過電話讓我去加班後,我就關了機,不想再接任何人的電話,想圖個安靜。”
“是的,他來了,妳怎麽想讓別人打擾呢?”
“妳無聊不無聊?壹大早跑上來就跟我吵架,我招妳了還是惹妳了?”
“是的,是我無聊。我他媽的真無聊,這麽好的房子不知道自己留著住,為的是啥?為的就是無聊?就是讓別人來這裏給我戴綠帽子?”
她突然站起來說:“吳國順,請妳放尊重點兒。我知道妳幫了我不少忙,我心存感激,我唯壹能做到就是以身相許,難道這還不夠嗎?是的,這是妳的房子,妳不提醒我也知道,我只是壹個過客,房子的主人是妳不是我。妳放心,我決不會賴在這裏的,至少我還有我的自尊,有我的人格。”
他木木地站著,不知說什麽是好,明明是自己壹肚子的委屈,到頭來反倒成了無理取鬧,對方卻成了受委屈的人。他不得不承認她的沈著冷靜,不得不承認她有很強的應變能力,輕描淡寫的幾句話就把他的質疑收攏起來,然後變成了攻擊他的炮彈,壹起拋向了他。他不知道是該給自己找壹個臺階下,還是迎著問題上。給自己壹個臺階下,必然要承認自己的不是,必然要哄她開心,那以後只能默認了她的這種態度,以後在她面前,只能是壹個窩囊的小男人。如果迎著問題上,必然會引發新的沖突,戰勝她,她將會服服帖帖地歸順妳,戰勝不了,很可能會弦斷帛裂。
他無法在短暫的時間內作出更合理的判斷,只感到心裏有股氣憋著出不來,便接了她的話說:“放尊重點兒?難道我對妳還不夠尊重嗎?田小麥,將心比心,妳想想,究竟是妳不尊重我,還是我沒有尊重妳?自從我倆相處以來,能幫的忙我沒有不幫的,能出的力我沒有不出的。妳提出十個要求,我滿足妳九個,有壹個滿足不了,妳就不高興了,妳就可以用另外的方式來傷害我,還說我無聊,說我不尊重妳。我們都是明白人,別揣著明白裝糊塗。”
“我真的不明白,妳究竟是咋啦?壹大早就來給我說這些,是什麽意思?妳讓我說什麽是好?”
他在田小麥壹連串的詰問聲裏,感到的是羞辱,自己像個無理取鬧的跳梁小醜。他感到了壹種莫名的憤怒和深深的失望,只好說:“好了,既然妳覺得我是無理取鬧,我走好了,我不該來,不該打破妳的平靜,不該幹擾妳的生活,行了吧?”
她沒有接他的話,屋子裏出奇地平靜了下來。他緩緩地向門口走去,就在打開門的壹瞬間,他多麽希望她來挽留自己,多麽希望她能從後面抱住自己,輕輕地說:“國順,妳別走,我不讓妳走。”如是,他會回過身來,狠狠地攬過她,要用她的身體把他窩在心裏的氣驅走。然而,她沒有吱聲,更沒有上來攬他的腰。他失望地打開了門,再回頭,看到她以手掩面,雙肩壹抖壹抖地哭泣著。他壹狠心,走了出去。
3.吳國順出手了
周壹早上剛上班,吳國順就接到辦公室通知,讓他次日去省城參加壹個有關文物保護的會議。吳國順“嗯”了壹聲,算是應允了。自從與田小麥吵過之後,他壹直很郁悶,正想找個地方去散散心,沒想到瞌睡遇到了枕頭,給了他壹個到省城開會的機會,也好回避壹下他與田小麥的矛盾,給雙方壹個冷靜的空間。
人往往就是這樣,吵過了嘴,才想起要說的話,打完了架,才想起學過的拳。那天從田小麥那裏回來後,他越想越生氣,越想越怨恨自己,明明讓人家給戴了綠帽子,還落了個無理取鬧的惡名,灰溜溜地出了門。他真沒想到田小麥這麽厲害,不動聲色地就將他擊敗了,讓他有氣無處使,有火無處發。他也真被她氣糊塗了,她說蘇正萬來送藥,他怎麽不看看茶幾上有沒有感冒藥?如果有,疑團可釋,如果沒有,那她不是不打自招嗎?還有,電視臺的職工很多,是不是每壹個職工病了他都會跑去送藥?如果不是,她與蘇正萬又是什麽關系?另外,這個地方是自己與她的秘密所在地,蘇正萬為什麽知道她住在這裏?應該把這壹個個的問題擺到她的面前,看她怎麽自圓其說。如果能說得清,倒也打消了他的疑團,如果解釋不清,那也好讓她當面表個態,她究竟是選擇蘇正萬,還是要選擇他?可是,當時他根本沒有想到這些,讓人家幾句話就把自己駁了回來,壹想起這些,他就感到窩囊憋屈。也罷,既然如此,只能等開會回來再說了。
吳國順到省城待了四天,開了兩天會,玩了兩天,沒有別的收獲,只是在飯局上聽到了壹個令他十分高興的消息,丁誌強被調到了省政協科教委當副主任,但金州市的市長人選還沒有定,有人說可能在金州內部產生,有人說可能要從省上派。無論怎樣,丁誌強被調走了,而且調到了壹個無關緊要的崗位,對他來講可是頭等的大好事,這就意味著姚潔失去了後臺,他就有可能把她徹底擊垮,奪回屬於自己的位子。
吳國順壹回到金州,就迫不及待地給何東陽打了壹個電話,何東陽說,他也聽說了,不過還沒有下文,究竟情況怎樣,現在還難說。他從何東陽的語氣中聽得出,他也很高興。這說明了兩個問題,壹是何東陽把他當成了自己人,才敢暴露真實的想法;二是這件事對他有利,對何東陽何嘗不是有利?權力的爭奪,往小裏說是個人與個人之間的爭奪,往大裏說是各個利益派別之間的爭奪。這個派別的帶頭人上去了,從上到下,大家都跟著沾光,如果這個派別的帶頭人被打壓下來了,或者是出了什麽問題,大家都跟著遭殃。現在,吳國順最想做的就是兩件事,壹是積極支持何東陽當上市長,二是把姚潔推翻。
這天下午上班,他剛給馬民打完電話,約好了下班後兩個人見面談談,沒料放下電話就聽到有人輕輕地敲了壹下門。他說了壹聲進來,壹個清麗的身影便推門走了進來,他壹看,原來是田小麥。自從上次吵過架後,壹晃十幾天過去了,雖然他還在記恨著她,但從內心還是期望能與她重歸於好。好幾次他編好了短信,要發時猶豫了,他不想主動認輸,不想給她慣下這個毛病,讓她始終掌握主動權,只好又放棄了。心裏卻壹直渴望她能主動打電話,這樣更讓他心理上能接受,面子上也能過得去。可他壹直沒有等來她的電話。現在,當她出現在面前時,他禁不住壹陣狂喜,無法抑制內心的激動,馬上站起來說:“妳終於來了,坐,坐吧!”
“不坐了,我還有事。這是房子的鑰匙,交給妳。”說著,遞過壹個信封,放在了桌子上。
他的腦袋“轟”地壹下,感覺壹片空白。待他回過神來,馬上問道:“妳這是什麽意思?”
“房子是妳的,我遲早得給妳騰出來,這幾天有時間就給妳騰開了。”
就在這壹刻,他覺得房子算個啥,什麽都不是,只有與他喜歡的人在壹起才是最重要的。他馬上接了她的話說:“小麥,妳應該冷靜壹下,不要因為幾句氣話就做出這樣的選擇。房子妳住去,如果妳覺得不踏實,改天過戶到妳的名下也行,別孩子氣了,好嗎?”
“謝謝妳壹直以來對我的關照,我會銘記在心的。這房子,我還是物歸原主吧。”說著,眼圈兒就紅了,轉過身快步走了出去。
頃刻之間,壹股涼氣從頭到腳灌了下來,吳國順沒有想到事情會來得這麽突然,更沒有想到兩年多的情感付出,孕育的卻是這樣的結果。他似乎能感覺到,田小麥之所以如此決斷,肯定有人當了她的堅強後盾,也肯定給了她承諾,或者是給了她壹個安定的居所,否則,她不會作出如此輕率的決定。而那個站在她身後的人,不言而喻,就是他的對手蘇正萬。
他點了支煙,狠狠地吸著,大口大口地吐著煙霧。他知道,事情到了這壹步,已經沒有挽回的可能了。這個世界就是這麽現實,今天妳有權,可支配別人,妳就是爺;明天妳失去了權力,受人支配時,妳就是孫子。他壹定要想辦法奪回他失去的,誰讓他過得不好,他也讓誰過得難堪。
晚上,吳國順與馬民在壹家羊肉館的小包廂裏見面了,兩人要了兩斤手抓,兩斤羊排,壹個小菜,壹瓶五糧液。吃喝好了,才進入正題。
“兄弟,哥想好了,量小非君子,無毒不丈夫。要幹大事業,就得有大氣魄。”
“對對對,哥說得對。”
“我是這樣想的,我們可以玩壹套局中局,制造壹封匿名信,信中就寫姚潔受賄,她在搞文化局舊樓的改造工程時收過邵大鵬的40萬,同時,她也收過妳的錢。”
“哥,妳這麽說,不就暴露我了嗎?”
吳國順特別不喜歡別人打斷他的話,就說:“妳急什麽急?聽完了我的話妳再說。”
馬民就不吱聲了。吳國順接著說:“這匿名信,要把邵大鵬的行賄數字寫具體,就說他為了從姚潔手裏得到工程,行賄40萬,還送了壹塊金表,然後再附上妳的那盤錄音帶。雖然是匿名信,因為有了證據,上面照樣會重視的。另外,這信上要多提到幾個老板,說他們也給姚潔行過賄,其中也有妳,至於這些老板是否真的行賄,行賄了多少,壹概模糊,不能說得太清楚。說到底,這只是壹個障眼法,如果不提壹下妳,邵大鵬肯定會懷疑是妳告的密,如果把妳也歸入行賄的行列之中,他就不會懷疑妳了。當然,這樣做不利因素也有,說不準檢察院的同誌還真的要把妳叫去談話,到時候妳壹口咬定沒有給她送過禮就行了。千萬不要承認,壹旦承認了,妳就完了。同時,那上面還提到了好幾個老板,不光是妳壹個,檢察院也不會盯著妳不放。”
馬民聽完,長出了壹口氣:“哥想得真周到。不過,我還是有點兒擔心,因為錄音上那些話邵大鵬只對我壹個人說過,等錄音帶公布後,邵大鵬肯定認為是我幹的,即便匿名信中有我的名單,也消除不了他對我的懷疑。”
“那也不壹定,他能對妳說,就不能對別人說?再說了,如果他對妳有所懷疑,妳就說檢察機關為了取證,他們可以在被調查人的身上安裝竊聽器,也可以在他常去的地方進行布控。妳再傻,也不可能自己告自己的狀,去接受檢察機關的審查。局中局,這裏面玩的就是智力和膽量。”
馬民恍然大悟道:“對了,我想起來了,那天我們隔壁桌子坐著壹男壹女,那男的正對著我們,不時朝我們這邊看,那女的壹直玩著手機。邵大鵬還悄悄說過,他們不會聽到我們說什麽吧?我說聽到了又能怎樣,管他什麽事?好,到時候邵大鵬如果懷疑我,我就把他們拉過來當替罪羊,就說肯定是那個女的錄了音,說不準他們就是檢察院的。”
吳國順舉起杯,說:“好,妳就這樣給他說,保證萬無壹失,定會成功。來,幹!”
喝了酒,馬民說:“哥的事就是我的事,有哥吃的肉,也會有我喝的湯。”
“放心好了,兄弟,我的翻身之日,就是妳的發財之時。無論是翻身,還是發財,必須掃清我們前進道路上的障礙,否則壹切都是空談。”
“哥說得對,我給妳掃……掃清,來,喝!”
兩人又喝了幾杯,吳國順怕馬民嘴上控制不好走漏風聲,便叮嚀說:“今天我們商量的事,妳任何人都不能透露。要記住,事成於密敗於疏。”
“哥妳放心好了,我知道哪個輕哪個重。”馬民正說著,手機響了,他接通後“餵”了壹聲,說:“我在外面喝酒,今晚不過去了,改天吧。”說完就掛了機。
“妳有事就忙去吧。”
“沒事。是小紅的電話,想叫我到她那裏去,今晚不去了,我要陪哥喝酒。”
吳國順知道,他說的小紅是壹家手機店的服務員,人長得很漂亮,明明知道馬民有老婆,還是願意當他的情人。吳國順由此及彼,想起田小麥,心裏頓感壹陣淒涼,不由得長嘆壹聲說:“小紅對妳不錯,妳要珍惜。”
“我看小麥對妳也不錯。要不,打個電話把她也叫來?”
吳國順搖了搖頭說:“已經散夥了。唉,算了,不提她了。”
“大哥好像有點兒舍不得?”
“有什麽舍不得的?舊的不去,新的不來,”
馬民嘿嘿壹笑:“就是,就是,散了就散了吧,舊的不去,新的不來,三條腿的驢不好找,兩條腿的美女多的是。深圳有個官員,為了包二奶,2005年買了壹套房子給二奶住,每個月給二奶5000塊錢,壹年6萬元,買房子花了50萬左右。今年跟二奶分開了,他把房子賣了,得錢200萬。算下來白玩女人五年,最後還賺了120萬塊錢,官員的妻子得知後臭罵官員說:‘妳怎麽只包壹個,多包幾個該有多好!’”
吳國順聽完哈哈壹笑,細細壹思謀,果然是這個道理。想想自己也是,如果把那套房子賣了,至少也能賣80多萬,減去買房款和付給田小麥的50多萬,等於白玩了她兩年多,還賺30萬元。有些事就是這樣,當妳朝著壹個方向想下去,越想越糾結,如果換種思維方式,卻豁然開朗。人生中也不妨有點兒阿Q的樂觀。也許馬民說得對,舊的不去,新的不來,三條腿的驢不好找,兩條腿的美女有的是。只要手裏有了權,送貨上門的多得是。
4.該爭取的就得積極爭取
丁誌強的調令終於以紅頭文件的形式發了下來,他被調到了省政協任科教委副主任。在丁誌強即將學習期滿的時候,省委作出了這樣的決定,除了讓他徹底脫離金州市,是不是還有別的意圖?何東陽揣測不透,但他心裏還是非常高興,仿佛壓在心裏的壹塊大石頭被搬開了,終於可以長長地透壹口氣了。
下午剛上班,何東陽收到了壹封匿名信,內容是檢舉揭發文廣局局長姚潔受賄之事,信中言之鑿鑿,說是中達裝潢有限公司經理邵大鵬為奪得文化局舊樓改造項目,向姚潔送了40萬元現金、壹塊金表,並說有錄音為證,錄音帶只寄給了紀委。信中還列舉到了另外幾個老板也向姚潔行過賄。何東陽看完,暗自壹笑,心想吳國順終於等來了機會,也抓到了機會。現實生活已經充分證明了這壹點,許多單位先是後院起火,引起了紀委檢察機關的重視,然後再根據群眾提供的線索順藤摸瓜,最終總能查出壹些腐敗問題來。從反腐的角度來講,壹個班子如壹味地講團結並不是好事,往好裏說是團結壹心,步調壹致,有利於工作,往壞裏想,有可能會壹團和氣,缺乏制約,走向集體腐敗。在民主化的進程中,需要不同的聲音,才有可能真正起到對權力的制約和對腐敗的監督作用,如果只有壹種聲音,反而有些不正常。
他輕輕地將匿名信合起來,又裝進了信封中。這樣壹枚小小的信封,有時候就可以改變壹個人的命運,或者就像壹顆炸彈,將壹個人幾十年辛辛苦苦經營起來的安樂窩炸個粉碎。他完全理解吳國順的心情,不這樣做,就意味著他要放棄許多;他這樣做,就有可能會得到許多。從這封信的內容,他已經掂出了它的分量,如果上面所說是真的,恐怕姚潔的人生從此將要改寫了,而吳國順取代姚潔的位子也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。他在心裏還是替吳國順感到高興,有了這樣壹個理由,他也好為吳國順說話了。
壹想到吳國順,又想起了上次他拿錢讓自己到省裏去活動的事。對這個問題,他不是沒有想過,主要是冒的風險太大,這個風險不僅是資金上的風險,還有政治上的風險。省裏的領導中,他私人交情不錯的只有原省政法委書記李茂堂,遺憾的是他去年退休了,現在就是想求他幫忙也幫不上了。另外比較熟悉的就是省長祝開運,前年他隨祝省長為代表的考察團去澳大利亞考察學習過壹回,但他們的關系也僅僅是熟悉而已,沒有更深的交往。如果貿然行事,搞好了可以得到祝省長的力挺,那他當市長就不成問題了;如果搞不好,不但會把事情辦砸,反而會給領導留下壹個不好的印象。何東陽正因為拿不準,才遲遲下不了決心。現在,他不能再猶豫了,機會來了,他必須要作出決斷,否則,過了這個村就不可能再有這個店了。他給吳國順打了壹個電話,讓他過來壹趟,他很想聽聽吳國順有什麽高見。
不壹會兒,吳國順來到了他的辦公室,壹進門就高興地說:“首長叫我來,肯定有好消息要告訴我。”
“做夢娶媳婦,想得美。坐,坐吧!”
吳國順坐在他對面的椅子上,笑著說:“要想就想些愉快的事,這樣生活才有希望。”
“妳說得沒有錯,做得也沒有錯,該積極爭取的,就得自己爭取!”
吳國順心照不宣地咧嘴壹笑說:“真佩服首長,什麽事都瞞不過妳。”
“我看過了,如果上面說的是真的,那可就是壹把撒手鐧。”
“絕對是事實,絕對經得起組織調查。”
“那就好,那就好。丁誌強調動的事正式下文了,估計他想庇護也不好庇護了,有了這樣的事,姚潔怕是難保了,到時候妳就可以取而代之。不過,這事壹定要沈住氣,不能讓人懷疑到妳。”
吳國順連連點頭稱是,說:“那……丁誌強壹走,市長的位子就該妳坐了。”
“哪有該不該的?給妳了就該,不給妳了就不該。這種搶手的位子,還不知有多少人盯著。”
“所以,我勸妳應該到省上去活動壹下,該出手時就出手,否則,錯失了良機可要後悔壹輩子。”說著,他又將那張儲蓄卡遞了過來,“這是40萬,先投石問路,然後我再給妳準備壹些。”
何東陽心裏熱乎乎的,兄弟畢竟是兄弟,共同的利益讓他們在大事面前總能保持壹致。問題是他現在對祝開運根本沒有把握,究竟祝開運是不是那種人?如果是,他又敢不敢接受?雖說是交易,如果關系不到那壹步,妳怕,對方也怕。妳怕他不接受,反而壞了妳的事;他怕妳不可靠,壞了他的名。如果祝省長接受了,那他的事肯定十拿九穩了,如果不是那種人,不接受,當面退給了他,那就意味著不但沒有希望,搞不好還會斷了前途。政治投資的特點是風險大,回報高,關鍵的問題就是要吃透對方,才不會馬失前蹄。而吃透對方,往往有很大的難度。想到這裏,他只好說:“有時我也很矛盾,太主動了怕冒風險;如果按兵不動,聽任自然,又怕被別人搶了先,感到冤枉。不過,妳剛才說的投石問路倒不失為壹個辦法,我可以考慮考慮。”
“那妳要抓緊,聽說韋壹光前幾天上省城開會了,我估計開會是個幌子,跑關系才是目的。”
“雞兒不尿尿,各有各的曲曲道。有關系的跑關系,沒有關系的就得找關系,現在的體制就是這樣,不跑不送,原地不動,可以理解。後天我到省上去開個會,順便看看情況。”
吳國順瞅了壹眼儲蓄卡說:“密碼是三個六三個九,如果不夠用,我再給妳打過去。”
“兄弟之間,感謝的話我就不用說了,就算妳借我的,以後再還給妳。”
“這‘借’字省了吧,用在我們之間多不好聽。”
何東陽笑了壹下說:“最好是兌換成美金,好用些。”說著將信用卡推到他面前。
“好的,明天我給妳送到家裏去。”
何東陽想了壹下說:“這種事,最好不要讓家裏人知道。妳就裝個紙袋,拎到我辦公室來吧,別人也不會註意到的。”
“我明白。”
1.家庭是最不講理的地方
幾天過後,那條老農被打的新聞已經在網上火爆起來了,許多地方報紙也做了轉載,整個事件查清了,打人者是南城區城管分隊副隊長胡亞生。何東陽聽到這個名字驚呆了,胡亞生?他的小舅子也叫胡亞生,這個打人的胡亞生會不會是他呢?
說到小舅子,他的確沒有多少好感,在上中學時就不好好學習,成天跟幾個小混混在壹起,不是喝酒滋事,就是上網玩遊戲。上大學無望,丈母娘求上門來,讓他給安排去當兵,將來退伍後好安排工作。他知道,現在城市當兵競爭很激烈,沒有特殊關系,想當兵也當不上。當兵已經失去原來的意義,由義務奉獻成了變相的曲線就業。他經不起丈母娘的嘮叨,更經不起胡亞娟天天吹枕頭風,最終還是安排小舅子當了兵。大前年退伍後,他的事情又來了。妻子胡亞娟受丈母娘的攛掇,讓他想個辦法把胡亞生安排到公安局去上班。
他有些不高興地說:“這是不是胡亞生的意思?”
胡亞娟說:“妳也知道,他沒有學下什麽東西,到別的地方去也不太合適,到公安局去抓個壞人、破個案子倒還行,他也喜歡幹那壹行。”
“妳告訴他,公安局屬於省公安廳直屬管理,他們要是沒有招人名額,我也辦不到。另外,市裏會對他們這些人做統壹安排,他發什麽愁?”
“這也不是愁不愁的事,誰不想著有個好壹些的工作?妳看著辦吧,反正是妳的小舅子,想幫就幫,不想幫也沒辦法。”
他不喜歡妻子用這樣的口氣跟他說話,更不喜歡丈母娘總是想利用他的關系走後門,卻不要求她的兒子去努力。沒過幾天,丈母娘叫他去吃飯。在飯桌上,胡亞生說:“姐夫,公安局進不去的話,暫時不進也行,聽我壹個戰友說,城管大隊現在缺人,妳就讓我去城管大隊吧。”
何東陽說:“妳們這壹批退伍軍人市裏已經做了統壹安排,壹部分人被安排到市化工廠去上班,壹部分人安排到市園林綠化隊。就這兩個單位妳選吧,選中哪個我可以幫妳說說。”沒想他的話還沒說完,丈母娘就不高興了。
丈母娘說:“要是在這兩個單位做選擇,他還求妳這個姐夫做啥?”老丈人重重地咳了壹聲,示意丈母娘不要再說下去了。何東陽假裝沒聽見,也不吱聲。這頓飯吃得很不開心,沒想到回了家,胡亞娟又跟他鬧起了別扭,說他當了副市長後,眼裏沒有她的家人。
何東陽生氣地說:“什麽話?沒有妳的家人我還上妳家做什麽?妳弟想當兵我就安排當兵,現在回來了,能統壹安排就業就不錯了,還挑三揀四的,妳們以為副市長的權力有多大?現在每個單位的編制都很緊,妳強行安排壹個人,跟著就會傳來壹大堆閑言碎語,妳們只顧自家的事,怎麽就不想想我的感受?”
“妳辦成辦不成也有句好話,哪有妳這樣的,壹句話就把人拒之於千裏之外了。難怪媽媽說妳,當了大官就瞧不起我們壹家人了。”
“這是什麽話?樣樣依了妳們就是瞧得起妳們?達不成妳們的心願就是瞧不起妳們?”
“妳看妳,還沒有說三句話,就妳們妳們的,這不是明顯地把我們壹家人與妳劃分開了嗎?還說不是哩。”他不想與妻子吵,只好說問問再看,還不知他們有沒有編制。
何東陽雖然心裏極不痛快,但又不想回家聽胡亞娟的嘮叨,只好勉為其難地將小舅了安排到了城管大隊,這才算平息了家庭內部的矛盾。當時他還考慮丈母娘家住東城,就把小舅子安排離家近壹些的地方,好對家裏有個照顧。
這個打人的胡亞生在南城,而且是分隊的副隊長,他的小舅子在東城,而且是壹個普通的工作人員,不可能是同壹個人吧。但是,現在既然事情發生了,他也管不了那麽多,只能對事,不能對人,如果真的是他的小舅子,也好讓他長長記性,先學學怎麽做人。
晚上回了家,胡亞娟正在收拾打扮,見他來了,就高興地說:“老公,我今天不做飯了,我媽鹵了妳最愛吃的豬蹄子,下午就給我打了電話,說讓我們壹起去吃。”
他心裏咯噔了壹下,馬上明白了,那個打人的胡亞生肯定是自己的小舅子,否則,丈母娘鹵豬蹄子也不會這麽湊巧。他知道丈母娘的飯好吃難消化,明明是鴻門宴,還必須要去,如果不去,必定會引發新的家庭矛盾。
來到丈母娘家,他壹進門就聞到了壹股濃濃的肉香味,那是丈母娘的拿手好戲,只有她才能調出那樣的味道,才能鹵出對他胃口的豬蹄子。與丈母娘和老丈人打過招呼後,胡亞生從裏屋出來了,也向他打了壹聲招呼。胡亞生長得高高大大的,看上去壹表人才,但是言談舉止中卻免不了有些小痞子的味道。
何東陽問:“最近工作還好嗎?”
胡亞生不好意思地笑笑,說:“還行。”
胡亞娟說:“還行什麽?現在成了名人了,都上網絡了,登報紙了。”
胡亞生的臉就刷的壹下紅了。
丈母娘說:“亂說什麽?吃飯吃飯。”
何東陽壹聽就明白了,他們不道破,他也不願意多問。
等壹大盆香噴噴的鹵豬蹄上了桌,胡亞生拿過塑料手套,給桌上每人發了壹雙。丈母娘說:“吃吧,趁熱吃,我鹵了壹大鍋,吃完了再上。”
何東陽看老太太挺辛苦的,等丈母娘落座後,不失時機地誇獎說:“我吃過的大餐也不少了,從沒有哪壹家的豬蹄子有媽做的這麽好吃。”
丈母娘經市長女婿壹誇,也高興地說:“那妳以後想吃了,就讓亞娟說壹聲,媽給妳們做。”
胡亞娟說:“媽,妳要拿壹手,不能他想吃了就做,等到他饞極了,才做壹頓,這樣他才吃不膩,每次都覺得好吃。”
丈母娘笑著白了壹眼胡亞娟,說:“妳還以為是從前,幾個月都吃不到肉,現在生活這麽好,普通人都不會饞極,他堂堂壹個市長能饞極?”
何東陽說:“那也說不準,多多每次來了,吃什麽都覺得不過癮,就想吃姥姥做的鹵豬蹄。”多多是何東陽的兒子,現在在省城讀大學,小的時候基本上都由姥姥帶著,從小就吃慣了姥姥做的飯菜,現在每次假期回來,就想吃姥姥做的飯。壹說到多多,老太太的話又多了,問他來電話了沒?身體怎麽樣?胡亞娟就接過話回答說,老太太為帶多多費了不少心血,對外孫的感情反而比我這個當媽的還深。何東陽聽得出來,胡亞娟明裏是貶自己,實際上是為了擡高她媽的功勞。不過話說回來,她說的也是實話,何東陽每每想起這些,覺得虧欠丈母娘的太多了,所以,有時丈母娘在他面前嘮叨上幾句,他也不太計較。
吃過飯,何東陽覺得該談正事了,就看著胡亞生,想問壹問他的副隊長是怎麽得來的,便說:“妳進步還挺快的,已經成了分隊副隊長了?”
胡亞生的臉壹紅,不好意思地說:“還不是在姐夫的關懷下才進步的嘛。”
何東陽立刻明白了,肯定是胡亞生打著自己的幌子走了關系,他們單位領導為了拍自己的馬屁才提拔了他,否則,憑他的表現根本不可能。他不想道破,又問:“剛才妳姐說妳上網絡上報紙是咋回事?”
胡亞生這才說:“姐夫,妳可要幫幫我。前兩天網絡曝出那個打了七旬老人的城管就是我……”
老丈人瞪了他壹眼,打斷他的話:“妳還好意思說,我的老臉都讓妳給丟盡了。”老丈人是個老實人,不愛說話。此刻,他能打斷話來指責兒子,說明他真是生氣了。
何東陽馬上打圓場說:“爸,妳別生氣,先讓亞生把話講完。”
胡亞生這才又說:“那天的事情是這樣的,那個老漢前壹次吆喝著毛驢車從主街道上過來的,我警告過他,這次他又走了這條路,我讓他拉回家去,並嚇唬他說,他要不返回去我就摔他的菜。我本來是想讓他承認錯誤,沒想這老漢太犟,說,妳敢?我就真摔了下去。他不幹了,上來扯住我的衣服,我才動手打了他兩個耳光。沒想到這件事鬧大了,不知被什麽人捅到了網上,雖然沒有提名道姓,但上面來人壹追查,還是查到了我。聽領導的意思,還要撤我的職,司法部門還要介入,這樣壹來,這飯碗能不能保住都很難說。”
何東陽說:“妳呀!妳是壹名執法人員,怎麽能動手打人?而且打的又是七十多歲的老人。現在惹出了禍,才知道後悔了?”
丈母娘說:“可不是嘛,他早就後悔了,這幾天飯都吃不下去了。如果飯碗真丟了,以後可咋辦?東陽,妳是當哥的,妳弟做得不對,妳批評教育,但無論如何別讓公安局抓進去。這壹抓進去,再放出來,人就不是原來的那個人了,工作沒了,對象也沒了,恐怕壹輩子都會在人前擡不起頭來。”
老太太繞了壹個大圈,就是想讓他為胡亞生幫幫忙,何東陽不好直接拒絕,就故意說:“妳們可能還不知道吧?那天,那個挨了打的老人家來市政府堵住了我的車,我親口答應了他,要查清楚這件事,對打人者要給予嚴懲。妳看妳,胡亞生,惹了這樣大的禍,也不早告訴我壹聲。”
老太太接了說:“他還不是怕給妳添麻煩嘛。現在紙包不住火了,只好求妳出面說說,讓他們單位內部批評教育壹下就行了,別再讓公安局插手了,怎麽說他也是多多的舅舅,妳就看在多多的面子上幫幫他吧。”老太太說著,就吸溜吸溜地哭了起來。
何東陽聽到她壹哭,心也軟了許多,雖然他對胡亞生的這種做法非常生氣,但他畢竟是孩子的舅舅,有了這層關系在裏面,許多東西想繞開也很困難。他只好勸慰老太太:“媽,妳別哭了。既然事情發生了,我們就盡量挽回。至於亞生的工作問題,我可以向妳保證,不會受到影響,別的方面,可能會受點兒影響,不過,吸取壹些經驗教訓也沒有什麽不好,讓他長點兒記性。”
胡亞娟也趁機說:“媽,妳放心吧。亞生只不過犯了這麽個小錯誤,還不至於被開除公職。再說了,東陽現在還在副市長這個位子上,只要他們知道亞生是東陽的小舅子,下面辦事的人就不會太過分。”
何東陽壹聽這話很不高興,胡亞娟怎麽這麽說話,這不是明顯地在鼓勵胡亞生為虎作倀嗎?他看了她壹眼,本想說幾句,又覺得這種場合說了不好,就沒有吱聲。
回到家裏,何東陽覺得有必要向胡亞娟提個醒,就問她:“胡亞生的副隊長是怎麽壹回事?”
“什麽怎麽壹回事?他表現不錯,單位領導覺得應該重用他,就提拔了他。”
何東陽正色說:“亞娟,妳給我說實話,妳是不是暗中走了關系?”
“什麽暗中走關系?說得難聽死了。我只不過在壹次偶然的機會見到了他們城管隊的隊長,向他問了壹下胡亞生的情況,希望他多多關照壹下,並沒有說讓他提拔。”
“亞娟,我給妳明確地說壹聲,以後不許妳再這樣。妳是領導幹部的家屬,妳這樣過問妳弟弟的領導,並叮囑他要關照妳弟弟,他會怎麽想?他肯定會認為妳想讓他提拔妳的弟弟,他不提,怕是我授意的;提吧,又勉為其難。傳出去,讓別人怎麽想?”
胡亞娟的臉上掛不住了,就說:“妳看妳,我既沒有提妳的名字,更沒有打妳的旗號,我只問問我弟的情況就不行了?難道我嫁了壹個副市長,我連關心弟弟的權利也沒有了嗎?”
何東陽盡量心平氣和地說:“不是說妳嫁了我就不讓妳關心弟弟,妳的弟弟也是我的弟弟,我不是不妳讓關心,但不是像妳這樣的關心,妳這不是真正的關心,而是害妳弟弟。”
胡亞娟“哦唷”了壹聲:“領導的話就是有水平,可我就是壹點兒也聽不懂,好像妳的關心才是真正的關心,別人的關心都是害人家?我問妳,妳關心他什麽啦?比起我媽媽關心妳兒子來,妳對亞生的關心能有多少?”
女人死攪蠻纏的時候,妳絕對不能順著她的話去說,否則,妳就會進到她那混亂的邏輯圈套中走不出來。他不接她的話茬,只講著道理說:“比如說,妳今天當著他的面說的那些話,就不應該,那樣愛他,會助長他的優越感,反而會害他。”
“哪些話?我說哪些話助長了他的優越感,會害了他?難道我們都是害他的,只有妳壹個人是關心他的嗎?”→文¤人·$·書·¤·屋←
“妳當著他的面說,只要他們知道亞生是東陽的小舅子,下面辦事的人也不會太過分。這種暗示性的話,對他沒什麽好處。”
“難道我說的不是真的?難道妳要否認他是妳的小舅子嗎?行!何東陽,何市長,妳要真的覺得有這樣壹個小舅子丟了妳的臉,影響妳升官,妳可以不認他,可以斷絕與他來往,但是妳沒有權力幹涉我認我的家人。”說著說著,竟然嗚嗚咽咽地哭了起來。
何東陽壹看胡亞娟這麽不講道理,無心再說了,只好連連說:“好了好了,越說越離譜了,什麽斷絕來往,什麽不認他,說這些傷感情的話做什麽?妳看電視吧,我到書房裏看壹會兒文件。”
何東陽雖然嘴上說得很平靜,心裏卻十分惱火,他沒有想到胡亞娟越來越俗不可耐,越來越不可理喻了。勞累了壹天,本來想在家庭這個溫暖的港灣裏小憩,之後再投入到明天的工作中,可誰知家庭有時候卻是壹個最不講道理的場所。晚年的托爾斯泰就是因為家庭不和諧,才發出了“人生最大的孤獨就是臥室裏的孤獨”的感嘆。
來到書房,他並不是想看什麽文件,而是想在這裏平靜壹會兒。他點了支煙,吸著,想著,覺得心裏有壹種說不出的委屈。要是壹個普通的工人、普通的公務員,遇上這麽不講理的老婆,可以同她吵,同她鬧,可他不能,他必須讓著她。正因為這壹而再、再而三的忍讓,讓她得寸進尺,越來越不可理喻。好在他的官不大,權力也有限,倘若他的官位再高壹些,權力再大壹些,說不定她還會幹出什麽事來。
第二天壹上班,秘書長潘多文敲開了他的辦公室,何東陽向他點了點頭,示意他坐下來說。
潘多文就坐在了辦公桌對面的椅子上,說:“我已經安排明天早上去鄉下慰問那位上訪的老人,讓城管大隊也去,順便讓他們買壹些滋補品帶上。我想請示壹下何市長,需不需要通知媒體參與?”
何東陽覺得潘多文不愧是秘書長,問題就是想得周到,便問他:“妳覺得有沒有必要通知他們去?”
潘多文說:“如果明天讓胡亞生壹同去的話,就不要通知媒體了,最好不要讓媒體知道具體的人。如果胡亞生不去,就讓媒體去報道壹下,也算是對社會輿論作壹個交代。”
何東陽知道潘多文完全是為了考慮胡亞生的聲譽才這麽安排的,便說:“解鈴還需系鈴人,讓他親自去賠禮道歉,老人家心裏會平衡些。再說了,這對胡亞生也是壹次吸取教訓的極好機會,不能讓他錯誤地認為,他是我的小舅子就可以為所欲為。”
“何市長也不必擔心,我已咨詢了有關司法部門,這只是工作方法上的不當,還構不成司法處理。另外,城管大隊領導也表態了,由他們批評教育就行了,司法部門沒有插手的必要。”
何東陽心裏當然清楚,潘多文在有意替他擔當,如果他們不知道胡亞生是他的小舅子,處理的結果遠遠不是這樣的。雖然他沒有有意授權於誰,而下面辦事的人都礙於他的面子,想把大事化小,小事化了。但任何事情都得有個限度,不能太過分了,太過分了,必然會引起民憤,必然會適得其反。想到這裏,便說:“光單位批評教育還不夠,必須要做出行政處分,這樣才好給社會壹個交代,對他本人也是壹次教育。他現在不是分隊的副隊長嗎?像他這樣,還怎麽繼續當?”
“我明白了,何市長,那我走了?”
“那妳去吧,該怎麽辦就怎麽辦,不要顧及我。”
潘多文走後,何東陽覺得輕松了許多。這件事如此處理,也算比較圓滿,既對社會輿論有了壹個交代,妻子壹家人也能接受。
剛點了支煙,還沒有吸上兩口,信訪辦的高永信匆匆進來了,他壹看高永信臉色不大對勁,就知道麻煩事又來了,忙問:“什麽事?”
高永信垂了頭說:“我幹了壹件壞良心的事。”
“什麽壞良心的事?”
“李瘋子患了癌癥,已經晚期了。那天我們幾個人把他送到精神病醫院後,醫生悄悄告訴我,他已經患癌癥了。放他出來,就是想讓他與家人、親友們最後聚聚,怎麽又把他送回來了?我壹聽傻眼了,只告訴醫生,要不是首長來視察,遇到這麽大的政治活動,我們也不會把他送回來的。回來的路上,我的心裏壹直很糾結,我都是快退休的人了,幹的什麽呀?我們的政府,為什麽這麽害怕聽到反面意見?為什麽這麽害怕上訪者?快回到金州時,我實在拗不過自己,就讓其他人回來了,我壹個人又去了趟醫院,親自把李瘋子給接回來了。回來後,我就與他的家人壹起把他送到了市醫院,檢查的結果是,癌細胞已經擴散了,估計他在人世的日子也不會太多了。”
何東陽心裏壹陣陣絞痛。“我們的政府,為什麽這麽害怕聽到反面意見?為什麽這麽害怕上訪者?”高永信的詰問像刀子壹樣剜著他的心,也常常困擾著他,他卻無言以對。在他所受的理論教育中,從來都是人民的利益高於壹切,要與人民群眾心連心,要接受群眾的監督。但理論與現實結合的時候,又成了另外壹回事。因為壹些反面意見,會影響到決策者的政治前途,如果接受了他們的意見,容忍了他們,就意味著要放棄自己的壹切,包括權力、地位,這就人為地加劇了領導者與被領導者之間的對立與矛盾。而他和高永信,在融入到這個利益集團之後,就會不自覺地維護這個團體的利益。維護團體的利益,其實也就是在維護自己的利益。正因為如此,他和高永信壹樣,無形中成了扼殺李瘋子的幫兇。說到底,他和高永信只不過是這個利益鏈條中的壹個節,誰都很難掙脫,除非妳要放棄所有的壹切。
高永信緩緩地從口袋中拿出壹張折疊整齊的紙,打開,放到了他的面前:“我最近身體不太好,老了,畢竟五十多歲的人了,想申請內退,希望組織能批準。”
何東陽的腦子“嗡”地壹下,他知道,這件事可能對高永信的觸動太大了,才下了決心要放棄所有的壹切,求得壹種心靈上的平衡。而事實上,這件事不僅對高永信,對他的內心也是壹次極大的沖擊。現在,李瘋子的生命已經無可挽回了,如果……高永信就這樣走了,他的心裏實在有些承受不起。畢竟,高永信是他的部下,他不能讓他帶著這樣壹顆破碎的心離開工作崗位,就此退休。他將退休報告輕輕推到高永信面前,說:“老高,其實我的心與妳壹樣。有些事,妳不願意,我也不願意,但這又不會因我們的主觀意誌而轉移,沒有辦法,誰讓我們在同壹個體制內?”
高永信又將內退報告推了過來,說:“正因為如此,我才想解脫,我再也不願意經受這種內心的折磨了,再也經受不起了。”
“老高,內退了,就能解脫妳內心的折磨嗎?不能的。有些,過後了才知錯,妳是,我也是。妳可以請假休息調整壹下,或者找個出差的理由,出去散散心。內退真的不行,放了妳,我的心裏更難受。”說著又將報告推到高永信的面前,“收起來吧,我再也不給妳添壓了。老高,人心都是肉長的,我給妳添壓的同時,我何嘗不是與妳壹樣的心情?”
2.月色中的野合
又是壹個雙休日,吳國順的老婆去參加老同學聚會,兒子到學校補課,他正好有了時間,就想與田小麥纏綿壹下。盡管他懷疑田小麥傍上了蘇正萬,想起來像吃了只蒼蠅壹樣惡心,但壹想到她的身體,想到她在床上的千呼萬喚,他就不由得壹陣興奮,全身充滿了活力。他恨她,又無法徹底放棄她。有時,就是帶著這種恨,在汗水與肉搏中又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愛。他由此而感慨,人真是個難以理解的怪物,心裏壹方面在恨她,另壹方面又想進入她。壹旦進入後,又覺得她是那麽的美好,是那麽的無可替代。
記得上次與她相約,是在壹個月前。他與幾個朋友喝酒時,收到了她的信息:“妳在幹嗎?”壹看到她的名字,心裏就壹陣莫名的激動,馬上回了信息:“與朋友喝酒。妳呢?在忙什麽?”信息馬上又來了:“我在金海馬唱歌,無聊死了。妳散夥了給我電話。”他壹看到這樣的信息,就知道她想見自己,只好對朋友說,有事要回家。壹個開車的朋友想放開膽量好好喝壹場,就把車鑰匙給他,妳開車去,明天早上,我到文廣局去取車。
吳國順完全有能力自己買壹輛車的,但他不想買。他現在還是體制中人,又是官員,太張揚會引起別人的猜忌。更重要的是,他還享有坐公車的權力,雖然這種權力暫時被人篡奪了,但隨著時間的推移,壹定會奪回屬於他的那份權威和尊嚴。
吳國順上車後,給田小麥發了壹條信息:“十五分鐘後,妳下樓,我來接妳。”發完信息,就開車上了路。金州的夜晚褪了白天的浮華,卻要比白天看起來陰柔了許多,閃爍的霓虹燈光中多了幾分曖昧色彩,讓人平添了壹種欲望的沖動。車繞過天橋,向南壹拐,就在很遠的地方看到了“金海馬”三個立體感很強的大字,在燈光變幻中放出不同的色彩。這個地方他過去經常來,都是老板們請他來唱歌。他特別不喜歡這種氛圍,為了不駁對方的面子,又不得不到這裏待壹會兒。現在,大權旁落後,昔日那些酒肉朋友壹個個遠離了他,飯局少多了,正好落個自在。車到金海馬門口的廣場,他壹眼就看到了等候他的田小麥。田小麥今天穿得特別隨意,上身著壹件白色長袖衫,下身穿著緊身黑色褲,腳蹬壹雙紫色長靴,外加壹個黃色披肩,壹個大包,高綰起發髻,整個人就顯得身材火辣而又高挑。
他將車開到她面前,打開窗戶說:“請吧,小姐。”
田小麥“哇噻”了壹聲,上了車才說:“沒想到我們家的小順子也玩起了酷,這是誰的車?”
吳國順忍不住咧起大嘴哈哈大笑了起來。
田小麥說:“傻笑個什麽?”
吳國順邊笑邊說:“妳怎麽叫我小順子?”
田小麥嘻嘻笑著說:“叫著覺得親切,好玩唄。”
“小順子是我的小名,這世上除了我們村裏的長輩這麽叫過我,還沒有人再敢這麽叫,真是個小妖精,沒大沒小的,以後不許叫。”
“原來是妳小名?真好玩!為啥不能叫?”
“讓人聽到了多不好?”
“原來妳也有怕?妳不讓我叫,我偏要叫,小順子,小順子……”
他被田小麥逗樂了,就嘿嘿笑著說:“小妖精,再叫看我怎麽收拾妳!”
田小麥就將頭湊過來悄悄說:“好呀,本姑娘等著妳收拾。”
“現在開車,等回到家裏再說。”
“妳還沒有回答我的話,這車是誰的?”
“是我壹個朋友的,他喝酒,怕出事,我只好把車開來了。”
“要不,開車兜兜風再回去,剛才在KTV烏煙瘴氣的,悶死了,是壹個老板請廣告部的客,他們硬拉上了我。”
吳國順壹聽心裏酸酸的。過去他在廣電局主事時,管理上很嚴格,絕不允許廣告人員吃廣告客戶的飯,決不允許記者搞有償新聞。沒想到,不到幾個月的工夫,物是人非,好不容易形成的良好風氣就這麽敗壞下去了。也罷,壹朝天子壹朝臣,等到自己坐鎮了,再來次廢舊革新。
田小麥見他沒有吱聲,便問:“妳在想什麽?”
他這才問:“到什麽地方去兜風?”
“我們去看看莊稼地好不好?”
“好的。”說著就將車開到了西環城公路上。這條公路上車輛不多,路的兩邊,壹邊是城市,壹邊是田野。白天,農村的人到城裏來逛街,晚上,城裏人又到田野來散步。時令到了秋天,天氣有點兒涼,田野裏的風景少了,來田野散步的人寥寥無幾。他把車開到田野的土路上,壹直開到了壹片小樹林裏,才與田小麥下了車。
秋天的月亮照著大地,微風壹起,旁邊的那片玉米就跟著搖曳了起來,發出沙沙的聲音。田小麥來到田埂上,高興地說:“真美喲,好壹片田園風光。”
吳國順隨口吟誦道:“郭外秋聲急,城邊月色殘。”
她接了道:“瑤琴多遠思,更為客中彈。”
“妳也會?”
“王昌齡的詩,過去讀過。”
他看了她壹眼,月色朦朧中,田小麥身材顯得越發火辣,胸脯挺得很高,腰呈壹抹弧,臀便自然地翹了。他不由自主地走過去,從後面攬腰抱住了她:“冷嗎?給妳暖和壹下。”
田小麥咯咯地笑著說:“不冷。”
“不冷也要抱!”
她故意將屁股撅了幾下,說:“我就知道妳想抱,抱抱抱,我讓妳抱!”
吳國順被她刺激得渾身膨脹了起來,想起小時候在鄉村看公馬和母馬交配時,小母馬總是要尥幾個下蹶子,公馬總是樂此不疲,壹直將母馬調戲得渾身發軟了,才能服服帖帖地讓公馬的擺布。其實,人與動物也有相同的壹面,也有主動與被動之分,經她這壹尥蹶子,反而刺激了他,他緊緊地攬著她的胸,親吻著她的頸項和耳朵。很快,聽到她的呼吸聲加重了,並且還發了壹聲細細的呻吟。而這呻吟聲,又讓他更加亢奮,扳過她的身子,壹下緊緊地親住了她那散發著香味的小嘴兒,兩個人的身體就從正面緊緊地貼到了壹起。他的手就從她衣服中摸了下去,光滑的背,細柔的腰,飽滿的臀,手到處,處處是風景。她的身子就這樣被他越摸越軟,還不時顫動著。他騰出手解她的褲扣,剛將褲子扒了壹截,她突然伸過手拉住說:“到家好嗎?”
“野外好,我們還沒有在野外好過,就在野外。”
“不會有人吧?”
他環顧了壹下四周,很安靜。他拿掉她的手,又將褲子朝下拉了壹截,他感到了從她身上散發出來的熱量,還有壹縷淡淡的體香。風從兩人的身上輕輕掠過,吹到玉米葉上沙沙作響,月光如水般灑在他們的身上,又被他們搖成了碎片。她輕笑著說,在這野外我還是第壹次,真刺激。他說,妳掉過身去更刺激。於是,她又掉過了身,他從後面抱緊了她。很快地,那呻吟聲就融入到了曠野的沙沙秋風中。
此後多日,吳國順壹想起那天晚上的野合,就會產生壹種莫名的興奮。場景的轉換,能讓人產生新鮮感。他想,有了這壹次,以後還可以繼續。他已經對田小麥的身體有了壹種依賴,這種依賴,就像酒鬼於酒、煙鬼於煙、賭徒於麻將壹樣。盡管他無法接受她與蘇正萬的曖昧,有時候想起來有壹種說不出的恨與痛,但壹想到她的身體,他還是止不住渴望與興奮。
這天早上,等妻子出了門,他就迫不及待地給田小麥打了壹個電話,沒想到她卻關了機。過壹會兒又打,還是關機。心裏便想,這小婊子是不是與蘇正萬在壹起鬼混?≮更多好書請訪問Zei8.me 賊吧電子書≯
吳國順壹想到蘇正萬,心裏就像吞了壹只蒼蠅。真是個垃圾,電視臺的美女如雲,他為什麽不勾引別的,偏偏來撬他的?不知是他有意挑釁,還是真的喜歡田小麥?無論是挑釁,還是真的喜歡,他都覺得蘇正萬不應該拆自己的臺,更不應該利用職務之便迫使女下屬就範。君子報仇,十年不晚。他想等自己的計劃成功了,放翻了姚潔,再來慢慢收拾蘇正萬,要讓他為此付出沈重的代價。
他的計劃正在實施過程中,三天前,馬民說他已經從邵大鵬那裏套來了話,邵大鵬給姚潔送過40萬元和壹塊金表。邵大鵬說,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,我給她的最終還是加在工程款裏。吳國順明白,權錢交易的背後就是政府來埋單。近年來,各地的豆腐渣工程層出不窮,這邊的橋梁剛剛倒塌,那邊的樓房又壓死了不少人,說到底,這都是腐敗引起的。他不能說自己有多麽幹凈,他也不是什麽好鳥,也曾利用手中的權力在工程建設中謀取過私利,但相比姚潔,他沒有這個女人那麽貪心,更沒有她那麽膽大包天。他問馬民錄音了沒有?馬民說音是錄了,就是怕這錄音流出去,邵大鵬決不會放過他。他覺得馬民說的也是,就點點頭讓馬民先把錄音帶保存好,千萬別丟失了,然後再想想有沒有別的辦法,既不能讓邵大鵬懷疑到馬民,還要把姚潔的事反映出來。
這可是壹顆定時炸彈,有了這顆炸彈,足以置姚潔於死地。他感到了必勝的把握,也看到了希望的曙光。
吳國順看了壹會兒電視,到了十點多,又給田小麥打了壹個電話,還是沒有開機。他內心裏產生了壹種按捺不住的沖動,他要直接到田小麥住的地方去找她,他要親自證實壹下自己的判斷,看看她究竟在幹什麽。是自己多疑,還是她有事?
出門叫了壹輛的士,不壹會兒就到了幸福花園小區。壹來到這個地方,他就心潮起伏,感慨萬千,在這個地方,他已經與田小麥好了兩年多了。在這兩年多的纏綿中,他在經濟上付出了很多,她家要買房子,他給了20萬,平時給她買這買那,也花了不少。有時候,經濟與感情是成正比的,經濟上付出得越多,情感上投入得也越大。情感不等於錢,但錢可以表達情感。錢是妳付出勞動得來的,是壹種價值的符號,妳完全可以用它謀取幸福。當妳把它付給某壹個人的時候,就意味著將妳的情感也投入到了其中,錢也就成了情感。壹個人,倘若他說在情感上付出了很多,但是從來舍不得在經濟上付出,妳會認為他說的是真的嗎?顯然不可信,因為他最愛的是錢,他把最愛的東西儲存起來,舍不得花在他所愛的人身上,這種愛充其量也只是口頭的愛,沒有變成真愛。倘若有壹天沒有了這愛,他只感到遺憾,決不會心痛,因為他沒有損失什麽。而對於吳國順來講,如果有壹天真的與田小麥分道揚鑣了,他不僅會感到遺憾,也會心痛,因為他付出過情感。
來到幸福花園裏面,看到人工湖中假山聳立,流水潺潺,花草卻有些敗謝,綠地有些微黃。北方的秋天,總給人壹種淡淡的淒涼。就在吳國順從人工湖中穿過時,他看到了壹輛黑色的小車從旁邊的小路上開走了,他壹眼就認出了車牌號,是蘇正萬的。霎那間,他血脈賁張,臉上壹陣發燒。婊子,真他媽的婊子!難怪她壹直關機,原來她是留蘇正萬在這裏過的夜。他在心裏恨恨地罵著,大步向她住的C號樓走去。記得他剛剛拿到這套房子的鑰匙時,第壹個想到的就是她,他寧可與老婆孩子住舊房,卻把豪華社區的房子讓給她,沒想到她卻把他的房子當成了與別的男人鬼混的場所,是可忍孰不可忍!他匆匆來到C號樓,正準備摁門鈴,聽到有人下樓來,他就等到那人出門的時候時直接進了門。到了八層,來到802號門前,他側耳聽了聽,裏面有電視的聲音,他這才摁了門鈴。
他的心咚咚咚地跳著,雖然他不知道接下來將會發生什麽事,但他知道在他與蘇正萬之間,沒有調和的余地,有他就沒有蘇正萬,有蘇正萬就沒有他。他必須讓她做出明確的表態,否則,就讓她滾蛋!
他聽到了開門的聲音,她的抱怨聲也從門裏傳出來:“妳怎麽又來了?是不是落下什麽東西了?”
“是的,我落下了東西。”
“怎麽是妳?”
“怎麽就不能是我?這是我的房子,我難道沒有來的權利嗎?”
她壹轉身,回到了房間。他進了屋,壹轉身,砰的壹聲關上了門,房間裏立刻充滿了火藥味。
田小麥穿著壹身睡衣坐在沙發上,茶幾上的煙灰缸裏殘留著幾只煙蒂。他渾身壹陣戰栗,過了半天才說:“他昨天在這裏過的夜?”
“沒有。”
“背上牛頭不認賬!我明明看到他開車出去了,還想抵賴?妳給我說,這煙頭是誰的?”
“我抵賴什麽?早上他打電話叫我去加班,我說我感冒了,他給我買了點兒感冒藥,送來坐了壹會兒。這有什麽奇怪的?”
“妳就編吧。妳早上壓根兒就沒有開過機,還打什麽電話,打妳個鬼!”
“妳這人怎麽這麽說話,他打過電話讓我去加班後,我就關了機,不想再接任何人的電話,想圖個安靜。”
“是的,他來了,妳怎麽想讓別人打擾呢?”
“妳無聊不無聊?壹大早跑上來就跟我吵架,我招妳了還是惹妳了?”
“是的,是我無聊。我他媽的真無聊,這麽好的房子不知道自己留著住,為的是啥?為的就是無聊?就是讓別人來這裏給我戴綠帽子?”
她突然站起來說:“吳國順,請妳放尊重點兒。我知道妳幫了我不少忙,我心存感激,我唯壹能做到就是以身相許,難道這還不夠嗎?是的,這是妳的房子,妳不提醒我也知道,我只是壹個過客,房子的主人是妳不是我。妳放心,我決不會賴在這裏的,至少我還有我的自尊,有我的人格。”
他木木地站著,不知說什麽是好,明明是自己壹肚子的委屈,到頭來反倒成了無理取鬧,對方卻成了受委屈的人。他不得不承認她的沈著冷靜,不得不承認她有很強的應變能力,輕描淡寫的幾句話就把他的質疑收攏起來,然後變成了攻擊他的炮彈,壹起拋向了他。他不知道是該給自己找壹個臺階下,還是迎著問題上。給自己壹個臺階下,必然要承認自己的不是,必然要哄她開心,那以後只能默認了她的這種態度,以後在她面前,只能是壹個窩囊的小男人。如果迎著問題上,必然會引發新的沖突,戰勝她,她將會服服帖帖地歸順妳,戰勝不了,很可能會弦斷帛裂。
他無法在短暫的時間內作出更合理的判斷,只感到心裏有股氣憋著出不來,便接了她的話說:“放尊重點兒?難道我對妳還不夠尊重嗎?田小麥,將心比心,妳想想,究竟是妳不尊重我,還是我沒有尊重妳?自從我倆相處以來,能幫的忙我沒有不幫的,能出的力我沒有不出的。妳提出十個要求,我滿足妳九個,有壹個滿足不了,妳就不高興了,妳就可以用另外的方式來傷害我,還說我無聊,說我不尊重妳。我們都是明白人,別揣著明白裝糊塗。”
“我真的不明白,妳究竟是咋啦?壹大早就來給我說這些,是什麽意思?妳讓我說什麽是好?”
他在田小麥壹連串的詰問聲裏,感到的是羞辱,自己像個無理取鬧的跳梁小醜。他感到了壹種莫名的憤怒和深深的失望,只好說:“好了,既然妳覺得我是無理取鬧,我走好了,我不該來,不該打破妳的平靜,不該幹擾妳的生活,行了吧?”
她沒有接他的話,屋子裏出奇地平靜了下來。他緩緩地向門口走去,就在打開門的壹瞬間,他多麽希望她來挽留自己,多麽希望她能從後面抱住自己,輕輕地說:“國順,妳別走,我不讓妳走。”如是,他會回過身來,狠狠地攬過她,要用她的身體把他窩在心裏的氣驅走。然而,她沒有吱聲,更沒有上來攬他的腰。他失望地打開了門,再回頭,看到她以手掩面,雙肩壹抖壹抖地哭泣著。他壹狠心,走了出去。
3.吳國順出手了
周壹早上剛上班,吳國順就接到辦公室通知,讓他次日去省城參加壹個有關文物保護的會議。吳國順“嗯”了壹聲,算是應允了。自從與田小麥吵過之後,他壹直很郁悶,正想找個地方去散散心,沒想到瞌睡遇到了枕頭,給了他壹個到省城開會的機會,也好回避壹下他與田小麥的矛盾,給雙方壹個冷靜的空間。
人往往就是這樣,吵過了嘴,才想起要說的話,打完了架,才想起學過的拳。那天從田小麥那裏回來後,他越想越生氣,越想越怨恨自己,明明讓人家給戴了綠帽子,還落了個無理取鬧的惡名,灰溜溜地出了門。他真沒想到田小麥這麽厲害,不動聲色地就將他擊敗了,讓他有氣無處使,有火無處發。他也真被她氣糊塗了,她說蘇正萬來送藥,他怎麽不看看茶幾上有沒有感冒藥?如果有,疑團可釋,如果沒有,那她不是不打自招嗎?還有,電視臺的職工很多,是不是每壹個職工病了他都會跑去送藥?如果不是,她與蘇正萬又是什麽關系?另外,這個地方是自己與她的秘密所在地,蘇正萬為什麽知道她住在這裏?應該把這壹個個的問題擺到她的面前,看她怎麽自圓其說。如果能說得清,倒也打消了他的疑團,如果解釋不清,那也好讓她當面表個態,她究竟是選擇蘇正萬,還是要選擇他?可是,當時他根本沒有想到這些,讓人家幾句話就把自己駁了回來,壹想起這些,他就感到窩囊憋屈。也罷,既然如此,只能等開會回來再說了。
吳國順到省城待了四天,開了兩天會,玩了兩天,沒有別的收獲,只是在飯局上聽到了壹個令他十分高興的消息,丁誌強被調到了省政協科教委當副主任,但金州市的市長人選還沒有定,有人說可能在金州內部產生,有人說可能要從省上派。無論怎樣,丁誌強被調走了,而且調到了壹個無關緊要的崗位,對他來講可是頭等的大好事,這就意味著姚潔失去了後臺,他就有可能把她徹底擊垮,奪回屬於自己的位子。
吳國順壹回到金州,就迫不及待地給何東陽打了壹個電話,何東陽說,他也聽說了,不過還沒有下文,究竟情況怎樣,現在還難說。他從何東陽的語氣中聽得出,他也很高興。這說明了兩個問題,壹是何東陽把他當成了自己人,才敢暴露真實的想法;二是這件事對他有利,對何東陽何嘗不是有利?權力的爭奪,往小裏說是個人與個人之間的爭奪,往大裏說是各個利益派別之間的爭奪。這個派別的帶頭人上去了,從上到下,大家都跟著沾光,如果這個派別的帶頭人被打壓下來了,或者是出了什麽問題,大家都跟著遭殃。現在,吳國順最想做的就是兩件事,壹是積極支持何東陽當上市長,二是把姚潔推翻。
這天下午上班,他剛給馬民打完電話,約好了下班後兩個人見面談談,沒料放下電話就聽到有人輕輕地敲了壹下門。他說了壹聲進來,壹個清麗的身影便推門走了進來,他壹看,原來是田小麥。自從上次吵過架後,壹晃十幾天過去了,雖然他還在記恨著她,但從內心還是期望能與她重歸於好。好幾次他編好了短信,要發時猶豫了,他不想主動認輸,不想給她慣下這個毛病,讓她始終掌握主動權,只好又放棄了。心裏卻壹直渴望她能主動打電話,這樣更讓他心理上能接受,面子上也能過得去。可他壹直沒有等來她的電話。現在,當她出現在面前時,他禁不住壹陣狂喜,無法抑制內心的激動,馬上站起來說:“妳終於來了,坐,坐吧!”
“不坐了,我還有事。這是房子的鑰匙,交給妳。”說著,遞過壹個信封,放在了桌子上。
他的腦袋“轟”地壹下,感覺壹片空白。待他回過神來,馬上問道:“妳這是什麽意思?”
“房子是妳的,我遲早得給妳騰出來,這幾天有時間就給妳騰開了。”
就在這壹刻,他覺得房子算個啥,什麽都不是,只有與他喜歡的人在壹起才是最重要的。他馬上接了她的話說:“小麥,妳應該冷靜壹下,不要因為幾句氣話就做出這樣的選擇。房子妳住去,如果妳覺得不踏實,改天過戶到妳的名下也行,別孩子氣了,好嗎?”
“謝謝妳壹直以來對我的關照,我會銘記在心的。這房子,我還是物歸原主吧。”說著,眼圈兒就紅了,轉過身快步走了出去。
頃刻之間,壹股涼氣從頭到腳灌了下來,吳國順沒有想到事情會來得這麽突然,更沒有想到兩年多的情感付出,孕育的卻是這樣的結果。他似乎能感覺到,田小麥之所以如此決斷,肯定有人當了她的堅強後盾,也肯定給了她承諾,或者是給了她壹個安定的居所,否則,她不會作出如此輕率的決定。而那個站在她身後的人,不言而喻,就是他的對手蘇正萬。
他點了支煙,狠狠地吸著,大口大口地吐著煙霧。他知道,事情到了這壹步,已經沒有挽回的可能了。這個世界就是這麽現實,今天妳有權,可支配別人,妳就是爺;明天妳失去了權力,受人支配時,妳就是孫子。他壹定要想辦法奪回他失去的,誰讓他過得不好,他也讓誰過得難堪。
晚上,吳國順與馬民在壹家羊肉館的小包廂裏見面了,兩人要了兩斤手抓,兩斤羊排,壹個小菜,壹瓶五糧液。吃喝好了,才進入正題。
“兄弟,哥想好了,量小非君子,無毒不丈夫。要幹大事業,就得有大氣魄。”
“對對對,哥說得對。”
“我是這樣想的,我們可以玩壹套局中局,制造壹封匿名信,信中就寫姚潔受賄,她在搞文化局舊樓的改造工程時收過邵大鵬的40萬,同時,她也收過妳的錢。”
“哥,妳這麽說,不就暴露我了嗎?”
吳國順特別不喜歡別人打斷他的話,就說:“妳急什麽急?聽完了我的話妳再說。”
馬民就不吱聲了。吳國順接著說:“這匿名信,要把邵大鵬的行賄數字寫具體,就說他為了從姚潔手裏得到工程,行賄40萬,還送了壹塊金表,然後再附上妳的那盤錄音帶。雖然是匿名信,因為有了證據,上面照樣會重視的。另外,這信上要多提到幾個老板,說他們也給姚潔行過賄,其中也有妳,至於這些老板是否真的行賄,行賄了多少,壹概模糊,不能說得太清楚。說到底,這只是壹個障眼法,如果不提壹下妳,邵大鵬肯定會懷疑是妳告的密,如果把妳也歸入行賄的行列之中,他就不會懷疑妳了。當然,這樣做不利因素也有,說不準檢察院的同誌還真的要把妳叫去談話,到時候妳壹口咬定沒有給她送過禮就行了。千萬不要承認,壹旦承認了,妳就完了。同時,那上面還提到了好幾個老板,不光是妳壹個,檢察院也不會盯著妳不放。”
馬民聽完,長出了壹口氣:“哥想得真周到。不過,我還是有點兒擔心,因為錄音上那些話邵大鵬只對我壹個人說過,等錄音帶公布後,邵大鵬肯定認為是我幹的,即便匿名信中有我的名單,也消除不了他對我的懷疑。”
“那也不壹定,他能對妳說,就不能對別人說?再說了,如果他對妳有所懷疑,妳就說檢察機關為了取證,他們可以在被調查人的身上安裝竊聽器,也可以在他常去的地方進行布控。妳再傻,也不可能自己告自己的狀,去接受檢察機關的審查。局中局,這裏面玩的就是智力和膽量。”
馬民恍然大悟道:“對了,我想起來了,那天我們隔壁桌子坐著壹男壹女,那男的正對著我們,不時朝我們這邊看,那女的壹直玩著手機。邵大鵬還悄悄說過,他們不會聽到我們說什麽吧?我說聽到了又能怎樣,管他什麽事?好,到時候邵大鵬如果懷疑我,我就把他們拉過來當替罪羊,就說肯定是那個女的錄了音,說不準他們就是檢察院的。”
吳國順舉起杯,說:“好,妳就這樣給他說,保證萬無壹失,定會成功。來,幹!”
喝了酒,馬民說:“哥的事就是我的事,有哥吃的肉,也會有我喝的湯。”
“放心好了,兄弟,我的翻身之日,就是妳的發財之時。無論是翻身,還是發財,必須掃清我們前進道路上的障礙,否則壹切都是空談。”
“哥說得對,我給妳掃……掃清,來,喝!”
兩人又喝了幾杯,吳國順怕馬民嘴上控制不好走漏風聲,便叮嚀說:“今天我們商量的事,妳任何人都不能透露。要記住,事成於密敗於疏。”
“哥妳放心好了,我知道哪個輕哪個重。”馬民正說著,手機響了,他接通後“餵”了壹聲,說:“我在外面喝酒,今晚不過去了,改天吧。”說完就掛了機。
“妳有事就忙去吧。”
“沒事。是小紅的電話,想叫我到她那裏去,今晚不去了,我要陪哥喝酒。”
吳國順知道,他說的小紅是壹家手機店的服務員,人長得很漂亮,明明知道馬民有老婆,還是願意當他的情人。吳國順由此及彼,想起田小麥,心裏頓感壹陣淒涼,不由得長嘆壹聲說:“小紅對妳不錯,妳要珍惜。”
“我看小麥對妳也不錯。要不,打個電話把她也叫來?”
吳國順搖了搖頭說:“已經散夥了。唉,算了,不提她了。”
“大哥好像有點兒舍不得?”
“有什麽舍不得的?舊的不去,新的不來,”
馬民嘿嘿壹笑:“就是,就是,散了就散了吧,舊的不去,新的不來,三條腿的驢不好找,兩條腿的美女多的是。深圳有個官員,為了包二奶,2005年買了壹套房子給二奶住,每個月給二奶5000塊錢,壹年6萬元,買房子花了50萬左右。今年跟二奶分開了,他把房子賣了,得錢200萬。算下來白玩女人五年,最後還賺了120萬塊錢,官員的妻子得知後臭罵官員說:‘妳怎麽只包壹個,多包幾個該有多好!’”
吳國順聽完哈哈壹笑,細細壹思謀,果然是這個道理。想想自己也是,如果把那套房子賣了,至少也能賣80多萬,減去買房款和付給田小麥的50多萬,等於白玩了她兩年多,還賺30萬元。有些事就是這樣,當妳朝著壹個方向想下去,越想越糾結,如果換種思維方式,卻豁然開朗。人生中也不妨有點兒阿Q的樂觀。也許馬民說得對,舊的不去,新的不來,三條腿的驢不好找,兩條腿的美女有的是。只要手裏有了權,送貨上門的多得是。
4.該爭取的就得積極爭取
丁誌強的調令終於以紅頭文件的形式發了下來,他被調到了省政協任科教委副主任。在丁誌強即將學習期滿的時候,省委作出了這樣的決定,除了讓他徹底脫離金州市,是不是還有別的意圖?何東陽揣測不透,但他心裏還是非常高興,仿佛壓在心裏的壹塊大石頭被搬開了,終於可以長長地透壹口氣了。
下午剛上班,何東陽收到了壹封匿名信,內容是檢舉揭發文廣局局長姚潔受賄之事,信中言之鑿鑿,說是中達裝潢有限公司經理邵大鵬為奪得文化局舊樓改造項目,向姚潔送了40萬元現金、壹塊金表,並說有錄音為證,錄音帶只寄給了紀委。信中還列舉到了另外幾個老板也向姚潔行過賄。何東陽看完,暗自壹笑,心想吳國順終於等來了機會,也抓到了機會。現實生活已經充分證明了這壹點,許多單位先是後院起火,引起了紀委檢察機關的重視,然後再根據群眾提供的線索順藤摸瓜,最終總能查出壹些腐敗問題來。從反腐的角度來講,壹個班子如壹味地講團結並不是好事,往好裏說是團結壹心,步調壹致,有利於工作,往壞裏想,有可能會壹團和氣,缺乏制約,走向集體腐敗。在民主化的進程中,需要不同的聲音,才有可能真正起到對權力的制約和對腐敗的監督作用,如果只有壹種聲音,反而有些不正常。
他輕輕地將匿名信合起來,又裝進了信封中。這樣壹枚小小的信封,有時候就可以改變壹個人的命運,或者就像壹顆炸彈,將壹個人幾十年辛辛苦苦經營起來的安樂窩炸個粉碎。他完全理解吳國順的心情,不這樣做,就意味著他要放棄許多;他這樣做,就有可能會得到許多。從這封信的內容,他已經掂出了它的分量,如果上面所說是真的,恐怕姚潔的人生從此將要改寫了,而吳國順取代姚潔的位子也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。他在心裏還是替吳國順感到高興,有了這樣壹個理由,他也好為吳國順說話了。
壹想到吳國順,又想起了上次他拿錢讓自己到省裏去活動的事。對這個問題,他不是沒有想過,主要是冒的風險太大,這個風險不僅是資金上的風險,還有政治上的風險。省裏的領導中,他私人交情不錯的只有原省政法委書記李茂堂,遺憾的是他去年退休了,現在就是想求他幫忙也幫不上了。另外比較熟悉的就是省長祝開運,前年他隨祝省長為代表的考察團去澳大利亞考察學習過壹回,但他們的關系也僅僅是熟悉而已,沒有更深的交往。如果貿然行事,搞好了可以得到祝省長的力挺,那他當市長就不成問題了;如果搞不好,不但會把事情辦砸,反而會給領導留下壹個不好的印象。何東陽正因為拿不準,才遲遲下不了決心。現在,他不能再猶豫了,機會來了,他必須要作出決斷,否則,過了這個村就不可能再有這個店了。他給吳國順打了壹個電話,讓他過來壹趟,他很想聽聽吳國順有什麽高見。
不壹會兒,吳國順來到了他的辦公室,壹進門就高興地說:“首長叫我來,肯定有好消息要告訴我。”
“做夢娶媳婦,想得美。坐,坐吧!”
吳國順坐在他對面的椅子上,笑著說:“要想就想些愉快的事,這樣生活才有希望。”
“妳說得沒有錯,做得也沒有錯,該積極爭取的,就得自己爭取!”
吳國順心照不宣地咧嘴壹笑說:“真佩服首長,什麽事都瞞不過妳。”
“我看過了,如果上面說的是真的,那可就是壹把撒手鐧。”
“絕對是事實,絕對經得起組織調查。”
“那就好,那就好。丁誌強調動的事正式下文了,估計他想庇護也不好庇護了,有了這樣的事,姚潔怕是難保了,到時候妳就可以取而代之。不過,這事壹定要沈住氣,不能讓人懷疑到妳。”
吳國順連連點頭稱是,說:“那……丁誌強壹走,市長的位子就該妳坐了。”
“哪有該不該的?給妳了就該,不給妳了就不該。這種搶手的位子,還不知有多少人盯著。”
“所以,我勸妳應該到省上去活動壹下,該出手時就出手,否則,錯失了良機可要後悔壹輩子。”說著,他又將那張儲蓄卡遞了過來,“這是40萬,先投石問路,然後我再給妳準備壹些。”
何東陽心裏熱乎乎的,兄弟畢竟是兄弟,共同的利益讓他們在大事面前總能保持壹致。問題是他現在對祝開運根本沒有把握,究竟祝開運是不是那種人?如果是,他又敢不敢接受?雖說是交易,如果關系不到那壹步,妳怕,對方也怕。妳怕他不接受,反而壞了妳的事;他怕妳不可靠,壞了他的名。如果祝省長接受了,那他的事肯定十拿九穩了,如果不是那種人,不接受,當面退給了他,那就意味著不但沒有希望,搞不好還會斷了前途。政治投資的特點是風險大,回報高,關鍵的問題就是要吃透對方,才不會馬失前蹄。而吃透對方,往往有很大的難度。想到這裏,他只好說:“有時我也很矛盾,太主動了怕冒風險;如果按兵不動,聽任自然,又怕被別人搶了先,感到冤枉。不過,妳剛才說的投石問路倒不失為壹個辦法,我可以考慮考慮。”
“那妳要抓緊,聽說韋壹光前幾天上省城開會了,我估計開會是個幌子,跑關系才是目的。”
“雞兒不尿尿,各有各的曲曲道。有關系的跑關系,沒有關系的就得找關系,現在的體制就是這樣,不跑不送,原地不動,可以理解。後天我到省上去開個會,順便看看情況。”
吳國順瞅了壹眼儲蓄卡說:“密碼是三個六三個九,如果不夠用,我再給妳打過去。”
“兄弟之間,感謝的話我就不用說了,就算妳借我的,以後再還給妳。”
“這‘借’字省了吧,用在我們之間多不好聽。”
何東陽笑了壹下說:“最好是兌換成美金,好用些。”說著將信用卡推到他面前。
“好的,明天我給妳送到家裏去。”
何東陽想了壹下說:“這種事,最好不要讓家裏人知道。妳就裝個紙袋,拎到我辦公室來吧,別人也不會註意到的。”
“我明白。”